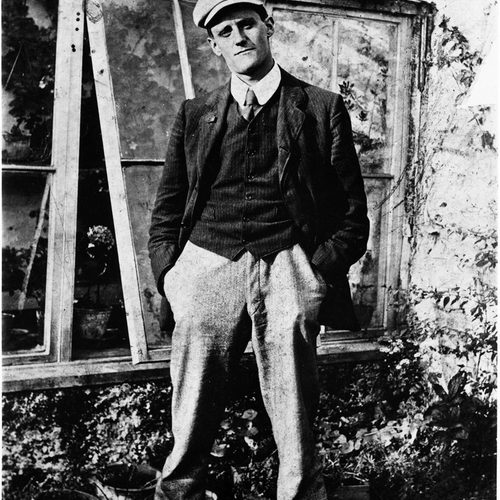波伏瓦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第二性》这本书,分为两卷,第一卷的标题是“事实与神话”,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女人变成他者的原因,侧重于思想性。第二卷的标题是“实际体验”,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对女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童年、青春期、性启蒙时期、婚后、为人母和步入老年后——进行全面考察。波伏瓦1908年出生,1929年获得巴黎大学哲学学位。41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二性》,这本书1952年被翻译成英文版。起初,人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高,第一卷太晦涩了,术语太多了,第二卷太鸡毛蒜皮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性》被评论为是“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即便没读过这本书,很多人也大概知道“第二性”是什么意思。

人们说起波伏瓦,总会先提到她和萨特的关系。比如1947年,《纽约客》杂志向美国读者介绍波伏瓦的时候,说她是“萨特身边的女知识分子”,“你见过的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比如1986年伦敦的《泰晤士报》说,在政治和哲学思考中,波伏瓦都追随萨特的指引。1990年,第一个给波伏瓦写传记的作者,也会说她是萨特的伴侣,说她“应用、传播、澄清、支持和践行”了萨特的“哲学、美学、道德和政治思想”。简单来说,她是位于从属关系的。后来有一位英国的哲学教授,给波伏瓦写了一本新的传记,题目叫《成为波伏瓦》,其主旨就是波伏瓦不只是萨特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这本传记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在萨特和波伏娃契约制关系中,到底谁是握有主动权的那一个。说起这两个人的关系,就逃不开一个八卦,那就是在萨特24岁,波伏瓦21岁的时候,两人确立了伴侣关系,但他们不想要那种彼此忠诚的传统关系,因此制定了一个契约,他们彼此是“本质的爱”,但准许对方同时拥有“偶然的爱”。这种开放式关系,刚开始是一个两年的契约,后来延续下去,到死后两人合葬在一起。波伏瓦写过四大本自传,但对自己的私生活有很大的保留。到她死后,她的日记和信件公开,人们才发现,波伏瓦有过女同性恋的关系,而且交往的恋人还是自己的学生,这些女生后来有的跟萨特又混在一起,波伏瓦给她的美国情人、作家纳尔逊写的信,可比给萨特的信热情得多。波伏瓦曾分析女性的性自主权是如何被剥夺的,她自己的性自主权没有被剥夺。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在很多现代女性看来,波伏瓦是一个理想榜样,她表明一个女人,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不受任何偏见的约束。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到,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自己的一生。波伏瓦的所作所为,很少受社会成见的约束,但她也知道自己哪些行为还是应该少说或者不说为妙。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在很多现代女性看来,波伏瓦是一个理想榜样,她表明一个女人,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不受任何偏见的约束。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到,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自己的一生。波伏瓦的所作所为,很少受社会成见的约束,但她也知道自己哪些行为还是应该少说或者不说为妙。
波伏瓦从小是个学霸,上学,教书,写书。在她求学期间,法国妇女还没有选举权,也不能在银行开设自己的账户,也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没什么保障。波伏瓦学习成绩很好,但也不会被男生当成智力上或者未来职业上的竞争对手,那时候法国大学中女生的比例是24%,女生的出路大多是到女子学校去当老师。为了获得教师资格,波伏瓦参加了一系列资格证书考试,在当年的哲学概论考试中,两个女生包揽前两名,第一名叫西蒙娜•薇依,第二名就是西蒙娜•波伏瓦,两个西蒙娜后来都成为女性知识分子的楷模。第三名叫梅洛•庞蒂,后来是法国的一位哲学家。 波伏瓦一心想读书,她的妈妈却希望她早点儿嫁人。十八九岁的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人生有一种无力感,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切都是强加在我头上的,最后我只能在我的生活放弃自己。”她还写道,“我想要的是一种能陪伴我一生,而不是吞噬我一生的爱。”波伏瓦叮嘱自己,“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

《致命女人》剧照
波伏瓦有一个闺蜜叫扎扎,出生在大户人家,两个人都喜欢哲学。扎扎喜欢读书,她的妈妈却不太乐意,妈妈早就给扎扎准备了25万法郎的嫁妆,认为找个合适的对象才是女人的出路,可女儿偏要去索邦大学读书。前面提到,那位在哲学概论考试中考了第三名的梅洛•庞蒂,波伏瓦介绍他认识了闺蜜扎扎,这是扎扎认识的第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这个年轻人身上寄托着扎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然而,就像俗套的伤感小说一样,扎扎的妈妈可不想让女儿嫁给梅洛•庞蒂,她让女儿从索邦大学退学,阻扰两个年轻人见面。1929年11月,扎扎去世。21岁的波伏瓦目睹了这一爱情故事的幻灭,“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本是少男少女的一种信仰,但爱与自由在一个墨守陈规的社会中异常罕见。波伏瓦对爱的疑虑,对人性虚无的感概,都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缓解。在扎扎葬礼前一天,波伏瓦哭了,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刚结识的男友萨特指责她,太感情用事了,太沉溺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波伏瓦说,“这并不是苦涩的眼泪,而是孕育着一股力量的眼泪,从眼泪中,我感觉到自己心里女神的崛起,那个从长眠中醒来的女神。” 《永不妥协》剧照 20年后,《第二性》出版。此时的波伏瓦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小说家,她有萨特这位伴侣,还有作家纳尔逊这样一个美国情人,她是杂志出品人,是女性知识分子偶像。但在《第二性》的导言中,波伏瓦写到自己对“女性”这个话题的犹豫和恼怒,她说,在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之前,她犹豫了很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许多传统的长篇大论出版,它们哀悼女性气质的丧失,告诉女性必须“当一个女人,保持女人的状态,成为一个女人”,于是她不愿意再被动接受,袖手旁观,要写这样一本书。人类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观察他人的身体,并根据他们的身体来建立等级制度,比如说奴隶制度,你是黑人,在某一个时间段,你很可能就是奴隶。在种族问题上,这个习惯很持久。那么在性别问题上呢?波伏瓦认为,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并且将她们归入另一个等级:第二性。
《永不妥协》剧照 20年后,《第二性》出版。此时的波伏瓦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小说家,她有萨特这位伴侣,还有作家纳尔逊这样一个美国情人,她是杂志出品人,是女性知识分子偶像。但在《第二性》的导言中,波伏瓦写到自己对“女性”这个话题的犹豫和恼怒,她说,在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之前,她犹豫了很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许多传统的长篇大论出版,它们哀悼女性气质的丧失,告诉女性必须“当一个女人,保持女人的状态,成为一个女人”,于是她不愿意再被动接受,袖手旁观,要写这样一本书。人类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观察他人的身体,并根据他们的身体来建立等级制度,比如说奴隶制度,你是黑人,在某一个时间段,你很可能就是奴隶。在种族问题上,这个习惯很持久。那么在性别问题上呢?波伏瓦认为,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并且将她们归入另一个等级:第二性。
 《黑天鹅》剧照
《黑天鹅》剧照
《第二性》原作972页,分为两卷,分别在1949年6月和11月出版单行本。为了宣传这本书,萨特和波伏娃主编的《现代》杂志,预先刊登了《第二性》第二卷中的部分内容。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女性的性启蒙》一章。这一章中,波伏瓦描绘了一种自由的、相互回馈的性行为的愿景,女性能够把自己视为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去享受性行为。波伏瓦说,女性应当拒绝被动顺从地接受非对等和互惠的男性欲望,而是应该在“爱、温柔和情欲”中与伴侣建立一种“对等互惠”的关系。只要存在性别之争,男性和女性的情欲不对称就会带来问题,如果女人能从男人那里满足欲望,又能获得尊重,这些问题就好办了。
这些话有点儿学术腔,但现在是现代女性的共识,性当然应该是“对等而互惠”的。然而在1949年,波伏瓦的这一主张受到了非议。小说家莫里亚克对波伏瓦的文章加以讽刺,莫里亚克说,波伏瓦的写作简直达到了下贱的极限,他说,在一本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的杂志上,波伏瓦女士讨论这种话题合适吗?莫里亚克给《现代》杂志一位资助人写信说,“你员工的阴道对我来说不是秘密了。” 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波伏瓦写的是色情文学。
 《性别之战》剧照
《性别之战》剧照
接下来,《现代》杂志发表了波伏瓦有关女同性恋的章节,杂志在报摊上卖得很好,但波伏瓦招来了一大波羞辱,她反对性方面的不平等,她指出许多女人被当作男性享乐的工具,女性的欲望和快感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人们骂她的词包括“饥渴、冷淡、淫荡、女色情狂、女同性恋”,还有人说她“流产过一百次”,是“未婚母亲”等等。在一片骂声中,《第二性》第一卷正式出版,销量惊人,第一周就卖出去22000本。波伏瓦在书中说,“生物学不是命运”,婚姻和生育也不是,各种文化都在加强和巩固压迫女性的“神话”,“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她必须在与男人的比较中,找到她能成为的可能性。”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开头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认为每个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成为的过程,所以第二卷中展示了女性对她们生活经历的描述,展示她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被“他者化”的过程。第二卷照样受到了一些男性知识分子的批评,有人指责波伏瓦恼怒于自己的自卑情结,有人说《第二性》全书充满了“怨恨的语气”,如果作者能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能更清晰的表达自己了。有评论说,作者太神经质,太沮丧了。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这本令人作呕的关于性倒错和堕胎的论辩。 《杀死伊芙》剧照不论遭遇什么样的批评和谩骂,《第二性》给波伏瓦带来了丰厚的稿费收入。她用稿费买了一台唱机和一些唱片,没事儿跟萨特一起听古典音乐。1951年11月,她给情人写信说,“我决定把我肮脏的心交给不像男人那么肮脏的东西,我要送给自己一辆漂漂亮亮的黑色汽车。”闺蜜扎扎的去世,多多少少算是《第二性》早年间的伏笔。波伏瓦的写作大多是自己的生活有关,她的小说《女宾》《名士风流》都是写自己小圈子的故事,她晚年照顾萨特,写了《告别的仪式》这样的纪念文章,也写了《老年研究》这样的思想性著作。
《杀死伊芙》剧照不论遭遇什么样的批评和谩骂,《第二性》给波伏瓦带来了丰厚的稿费收入。她用稿费买了一台唱机和一些唱片,没事儿跟萨特一起听古典音乐。1951年11月,她给情人写信说,“我决定把我肮脏的心交给不像男人那么肮脏的东西,我要送给自己一辆漂漂亮亮的黑色汽车。”闺蜜扎扎的去世,多多少少算是《第二性》早年间的伏笔。波伏瓦的写作大多是自己的生活有关,她的小说《女宾》《名士风流》都是写自己小圈子的故事,她晚年照顾萨特,写了《告别的仪式》这样的纪念文章,也写了《老年研究》这样的思想性著作。
《伦敦生活》剧照
《第二性》出版之后,有一对英国出版商夫妇正在巴黎访问,他们听到这本书引起的争议,就想着把这本书赶紧翻译成英文。出版商夫妇的法语不是特别好,他们就请一位动物学教授审读法文版。为什么会请一位动物学教授审读呢?因为第一卷开头部分,正是从生物学角度来描述女性的,列举了大量的动物学事实,出版商夫妇大概只看了个开头,他们认为波伏瓦患有“言语上的腹泻”,太没有节制了,就请动物学教授来翻译并且大幅删减。动物学教授也不含糊,看完之后说,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的书,这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大刀阔斧删去15%的内容,《第二性》最初的英文版删去了78位女性的名字,删去了涉及女性愤怒和受到压迫的内容,也删减了波伏瓦对家务劳动的分析。尽管出了个删节版,波伏瓦关于“独立女性”的观点还是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如果一个女性想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第二性》是少数几本可以给她帮助的书籍之一。波伏瓦接受的哲学教育和文学教育在《第二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她引用古希腊剧作家的作品、罗马哲学家的作品,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的哲学和神学写作,大量的英法文学作品、信件和日记以及精神分析的记录,她用现象学的方法和存在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内容。有许多读者给她写信抱怨说,这本书写得太晦涩了,一位读者是这样说的:“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为了让少数人去研究形而上学和存在主义的深奥术语吗?还是为了让拥有常识和理解力的公众来解决这类问题?你就不能放弃所谓专业哲学家的迂腐,用生活的语言来表达吗?” 这些批评大多是针对第一卷的,到第二卷,波伏瓦的叙述就与第一卷截然不同。第一卷分为三部,题目分别是命运、历史和神话。命运这部分,波伏瓦讨论生物学论据、精神分析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女性。历史这部分,波伏瓦对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到近代的女性地位进行了一番梳理。神话这部分,波伏瓦分析了神话中的女性,她说,女人被视为母亲、妻子和抽象的概念,这些形象时而相混,时而相互对立,每一种形象都有双重面貌,在神话故事和男作家的叙述中,女性总是显得很神秘。《第二性》的第一卷的确有些难读,但其中有些问题,今天我们说到女性主义,还是会面对。比如月经羞辱这个问题,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波伏瓦在开头的生物学证据中说,女人与其说是在适应自身,不如说是适应卵子的需要,从青春期到绝经,女性月经都是整个机体在行动,它伴随着激素的分泌,调控着甲状腺和垂体,女性会脉搏加快、腹部疼痛,还可能有便秘。听力或视力出现紊乱,会头痛,比平时更容易激动,更神经质,更喜怒无常。这是生物学的现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对母亲来说,生女孩是耻辱的。《圣经•利未记》记载,希伯来人生下女儿,净身的时间要比生下男孩长两倍。《利未记》中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在埃及,小姑娘初潮之日,有严厉的禁忌,女孩子月经初潮期间会受到禁闭,打发到村子外面的小屋子里,亲人不能去看望她,她不能用手去触碰食物,母亲和姐妹可以用一个工具喂她进食,在这一期间,她接触过的东西都要烧掉。 《小妇人》剧照公元77年,罗马人普林尼的《博物志》说,“来月经的女人会糟蹋庄稼,使园子凋零,扼杀胚芽,使果实落地,杀死蜜蜂,如果她碰到酒,酒就变成醋,奶也会变酸。”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一份学术报告说,一旦来月经的女人碰到肉,肉就会腐烂。作者说他是在火腿厂里研究了真实案例,得到的结论。在19世纪,法国北部的造糖厂,禁止来月经的女人进入工厂,因为糖会变黑。这不是对血的一般厌恶,而是对月经的特别的厌恶,比如在沙戈民族中,女孩子要保证自己的经血不被人看到,“不要让你的父亲,兄弟和姐妹看到,如果你让人看到了,这是一个罪过。不要给你母亲看到,她看到会死去”。并非由于月经是血,而是月经从生殖器官里流出来,人们甚至不了解月经的准确作用,但通过月经的禁忌,男人表达了对女性生育所感到的恐惧。第二个问题——反女性主义者会说,女性从来没有创造出伟大的东西,她们天生就不如男人。19世纪,法国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叫蒲鲁东,他是一个“大直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女人就应该被禁锢在家中,他有一句名言是,“要么当家庭主妇,要么当妓女”。他说,女人就应该从属于男人,只有男人才算是社会个体,女人是低于男人的,她的体力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她的智力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她的精神也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在体力、精神和心灵这三方面,男人的得分是三乘三乘三,二十七,女人的得分是二乘二乘二,得分为八。我们不知道蒲鲁东为什么在这里要用乘法,而不是加法,反正他认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仅等于一个男人价值的8/27。蒲鲁东此言一出,就遭到了法国妇女的反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化界已经有许多出色的女性,主持着沙龙,掌控着言论。这场口舌之争是发生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的。 波伏瓦在“历史”的这一部分,概述了千百年来女性所受到的贬低与抑制。她说,反女性主义者从历史中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女人从来没有创造出伟大的东西;第二,女人的处境从来没有阻止伟大女性的成长。这两个断言是相互矛盾的,女性的成功很少见,恰好证明了时势对女人是不利的。生育的束缚和家庭劳动的负担,对女人来说,远远比男人沉重,女人要求新的地位是希望在她们身上,超越性能够压倒内在性。她说,按照恩格斯的理论,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改变了生产力的平衡,由此女人的劣势地位被确定下来。但这样说是不够的,这种劣势本身不足以解释她忍受的压迫。对女性来说不利的是,她没有成为一个劳动伙伴,而是被排除出人类的共在,认为女人是弱者,生产能力低一等,都不能解释这种排除。男性不再承认她是一个同类,女人不能把工具带来的希望变成自身的希望。
《小妇人》剧照公元77年,罗马人普林尼的《博物志》说,“来月经的女人会糟蹋庄稼,使园子凋零,扼杀胚芽,使果实落地,杀死蜜蜂,如果她碰到酒,酒就变成醋,奶也会变酸。”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一份学术报告说,一旦来月经的女人碰到肉,肉就会腐烂。作者说他是在火腿厂里研究了真实案例,得到的结论。在19世纪,法国北部的造糖厂,禁止来月经的女人进入工厂,因为糖会变黑。这不是对血的一般厌恶,而是对月经的特别的厌恶,比如在沙戈民族中,女孩子要保证自己的经血不被人看到,“不要让你的父亲,兄弟和姐妹看到,如果你让人看到了,这是一个罪过。不要给你母亲看到,她看到会死去”。并非由于月经是血,而是月经从生殖器官里流出来,人们甚至不了解月经的准确作用,但通过月经的禁忌,男人表达了对女性生育所感到的恐惧。第二个问题——反女性主义者会说,女性从来没有创造出伟大的东西,她们天生就不如男人。19世纪,法国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叫蒲鲁东,他是一个“大直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女人就应该被禁锢在家中,他有一句名言是,“要么当家庭主妇,要么当妓女”。他说,女人就应该从属于男人,只有男人才算是社会个体,女人是低于男人的,她的体力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她的智力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她的精神也只有男人的三分之二,在体力、精神和心灵这三方面,男人的得分是三乘三乘三,二十七,女人的得分是二乘二乘二,得分为八。我们不知道蒲鲁东为什么在这里要用乘法,而不是加法,反正他认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仅等于一个男人价值的8/27。蒲鲁东此言一出,就遭到了法国妇女的反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化界已经有许多出色的女性,主持着沙龙,掌控着言论。这场口舌之争是发生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的。 波伏瓦在“历史”的这一部分,概述了千百年来女性所受到的贬低与抑制。她说,反女性主义者从历史中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女人从来没有创造出伟大的东西;第二,女人的处境从来没有阻止伟大女性的成长。这两个断言是相互矛盾的,女性的成功很少见,恰好证明了时势对女人是不利的。生育的束缚和家庭劳动的负担,对女人来说,远远比男人沉重,女人要求新的地位是希望在她们身上,超越性能够压倒内在性。她说,按照恩格斯的理论,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改变了生产力的平衡,由此女人的劣势地位被确定下来。但这样说是不够的,这种劣势本身不足以解释她忍受的压迫。对女性来说不利的是,她没有成为一个劳动伙伴,而是被排除出人类的共在,认为女人是弱者,生产能力低一等,都不能解释这种排除。男性不再承认她是一个同类,女人不能把工具带来的希望变成自身的希望。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在有产阶级中,女人的附属总是最具体的,男人在社会和经济上越强大,在家长制家庭中就越有权威,男人乐意要多少妻子就可以有多少妻子,丈夫可以随便休妻,社会几乎不会给她们任何保护。双方赤贫倒是让夫妻关系变成更相互依存的关系。机器的广泛使用摧毁了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劳动阶级的解放,相应的推动了妇女的解放。但回溯历史,女性很有经济独立的时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财产继承权。正是由于工业的突飞猛进,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男性劳动所能提供的数量,女性在工厂中生产,摆脱了家庭,才获得了经济地位。19世纪初期,妇女比男性劳动者更屈辱地受到剥削,女性温柔恭顺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的因素。请注意,波伏瓦的论述不是以论辩的口吻进行的,也不是以论辩来结构的,她分析由男人造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我们经常会说,“你这样看问题,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波伏瓦说,“我这样看问题,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人。”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在有产阶级中,女人的附属总是最具体的,男人在社会和经济上越强大,在家长制家庭中就越有权威,男人乐意要多少妻子就可以有多少妻子,丈夫可以随便休妻,社会几乎不会给她们任何保护。双方赤贫倒是让夫妻关系变成更相互依存的关系。机器的广泛使用摧毁了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劳动阶级的解放,相应的推动了妇女的解放。但回溯历史,女性很有经济独立的时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财产继承权。正是由于工业的突飞猛进,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男性劳动所能提供的数量,女性在工厂中生产,摆脱了家庭,才获得了经济地位。19世纪初期,妇女比男性劳动者更屈辱地受到剥削,女性温柔恭顺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的因素。请注意,波伏瓦的论述不是以论辩的口吻进行的,也不是以论辩来结构的,她分析由男人造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我们经常会说,“你这样看问题,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波伏瓦说,“我这样看问题,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人。”
 《妇女参政论者》剧照
《妇女参政论者》剧照
波伏瓦回溯历史,她说自己得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整个妇女历史是由男人写就的。她说,在美国,没有黑人问题,这是一个白人问题,同样,“反犹不是一个犹太人问题,是欧洲人的问题”,妇女问题也是一个男人问题。男人以体力获得精神的威信,他们创造价值、风俗和宗教,他们总把女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并没有从女人的利益出发去做决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需要。正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制度导致对已婚女子的监护,也正是男人实现的技术变革解放了今日的妇女,正是男人伦理观的改变,导致许多家庭通过“节育”来控制人口,使一些女性能从生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人的,男人具有统治女人的意愿。 《第二性》的第二卷是非常生活化的。波伏瓦开篇写的就是童年,她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她说,在西方社会里,一般要求女性蹲下来小便,而站立姿势留给男性。对小女孩来说,这种差异是最明显的性别差异。小便时,她必须蹲下,露出屁股,避开人,这是一种羞耻的和不方便的束缚。在男孩身上,排尿功能就像是自由的游戏,具有一切活动自如的游戏所拥有的魅力。波伏瓦由精神分析入手,分析男孩和女孩的不同,她接着使用语言分析,小姑娘喜欢布娃娃,打扮它,就像梦想自己被喜欢被打扮那样,女性和布娃娃的相似一直保持到成年,在法语中,人们常会称呼一个女人为“布娃娃”,在英语中,人们把打扮的女人称为“打扮漂亮的布娃娃”。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波伏瓦说,自恋在女孩身上出现的特别早,在女人的一生中将起到头等重要的作用。“被动性”是女人从小时候起就在身上发展起来的特性,这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根据,而是教师和社会强加给她的命运,人们向她灌输,你要讨人喜欢,必须放弃自主,女人越是在世界上找不到资源,她就越不敢确认自己是主体。她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有时会隐藏不住他们更喜欢男孩儿而不是女孩儿,大多数父母期望有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对男孩儿说话时更加庄重,承认他们有更多的权利。女孩子在家中能感到父亲的权威,孩子越成熟,其世界越扩展,男性的优势就更加确立。女孩子学到的历史和文学知识都在确立这种等级观念。波伏瓦接下来写青春期少女的迷茫,写她们对月经的担忧,对遭遇强暴的恐惧,写她们用嘲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写她们的性启蒙。然后她写到“已婚女人”——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独身女人的定义就是由婚姻而来,不论她是受挫折的、反抗过的,甚或是对这种制度毫不在乎的。新娘得到的许诺并不是爱情,而是幸福的理想,她要将自己的世界封闭在她要负责管理的家庭之内,幸福的理想以物质的形式体现在住宅上,家正是在墙内构成了一个孤立的单位,家概括了资产阶级的一切价值,对往昔的忠诚,耐心,节俭,有预见,保证家人幸福是女人的任务。正是通过家务劳动,女人成功占有了自己的巢穴,她在管理家庭时表现出了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没有让她摆脱内在性,也不允许她确定自己的特殊性。我们看看波伏瓦是怎么说家务活儿的,“很少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西弗的酷刑,日复一日,必须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服,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变得衰老,她仅仅在延续现状,她没感到获得积极的善,而是无休止地与恶做斗争。这种一种每天重新开始的斗争。”波伏瓦在书中引用了很多文学作品来做分析和阐释,包括法国作家科莱特、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材料是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的日记。在许多“大直男”看来,索菲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料理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让托尔斯泰在婚后写出了两部伟大作品《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夫妇两人对如何处理财产发生矛盾时,索菲亚就变成了落后的女人,等托尔斯泰年老、离家出走,索菲亚的形象就变成了“母老虎”,但波伏瓦提醒我们注意这个被大文豪遮蔽的女性,她的日记不是《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名著,但却记录了一个已婚女人的心路历程。索菲亚在新婚之后的日记中这样说,“我不断觉得我要死了。这很古怪,现在我有了一个丈夫。我听到他睡着了,我独自一人感到害怕。他不让我进入他的内心,这使我难过。所有这些肉体关系令人恶心。”在婚礼一年后,索菲亚这样说,“他老了,注意力太集中了。而我呢,如今我感到自己这样年轻,我那么想做出疯狂的事!我不但不想睡觉,我反而想单足旋转跳舞,但是,和谁呢?暮气沉沉的气氛笼罩着我,我周围的人都是年老的。我竭力压抑每一个青春的冲动。”等索菲亚经历了怀孕生子,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九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阶段,至于第十个月,最好不要谈。一切都完成了。我分娩了,我有过自己的痛苦,我振作起来,我带着恐惧和对孩子、尤其是对丈夫持续不断的不安逐渐回到生活中。我身上有某种东西破裂了。有一样东西对我说,我会持续地受苦,我相信,这是对不能完成家庭责任的担心。”波伏瓦分析说,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她说,索菲亚•托尔斯泰的歇斯底里是意味深长的,“大直男”会说索菲亚是个泼妇,一哭二闹三上吊,在她的日记里,她显得既不慷慨,也不真诚,我们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但她一生都通过不断的指责,在忍受做爱、怀孕、孤独以及丈夫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她没有武器,却有敌对的意愿,她以软弱无力的意志加以拒绝,假装自杀、假装逃跑、假装生病,对她周围的人来说,这都是可恶的,她几乎看不到别的出路,也没有任何积极的理由来压制自己的反抗情绪。 《第二性》第二卷,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写成长,第二部写处境,从结婚写到老年,第三部题为辩解,写恋爱的女人,写自恋的女人,第四部写独立的女人走向解放。波伏瓦时常以女字旁的“她”或者“她们”来展开叙述,很多时候,这个“女子旁”的叙述显现出了女性的整体困境,我们来看几句书中的原文——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波伏瓦说,自恋在女孩身上出现的特别早,在女人的一生中将起到头等重要的作用。“被动性”是女人从小时候起就在身上发展起来的特性,这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根据,而是教师和社会强加给她的命运,人们向她灌输,你要讨人喜欢,必须放弃自主,女人越是在世界上找不到资源,她就越不敢确认自己是主体。她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有时会隐藏不住他们更喜欢男孩儿而不是女孩儿,大多数父母期望有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对男孩儿说话时更加庄重,承认他们有更多的权利。女孩子在家中能感到父亲的权威,孩子越成熟,其世界越扩展,男性的优势就更加确立。女孩子学到的历史和文学知识都在确立这种等级观念。波伏瓦接下来写青春期少女的迷茫,写她们对月经的担忧,对遭遇强暴的恐惧,写她们用嘲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写她们的性启蒙。然后她写到“已婚女人”——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独身女人的定义就是由婚姻而来,不论她是受挫折的、反抗过的,甚或是对这种制度毫不在乎的。新娘得到的许诺并不是爱情,而是幸福的理想,她要将自己的世界封闭在她要负责管理的家庭之内,幸福的理想以物质的形式体现在住宅上,家正是在墙内构成了一个孤立的单位,家概括了资产阶级的一切价值,对往昔的忠诚,耐心,节俭,有预见,保证家人幸福是女人的任务。正是通过家务劳动,女人成功占有了自己的巢穴,她在管理家庭时表现出了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没有让她摆脱内在性,也不允许她确定自己的特殊性。我们看看波伏瓦是怎么说家务活儿的,“很少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西弗的酷刑,日复一日,必须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服,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变得衰老,她仅仅在延续现状,她没感到获得积极的善,而是无休止地与恶做斗争。这种一种每天重新开始的斗争。”波伏瓦在书中引用了很多文学作品来做分析和阐释,包括法国作家科莱特、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材料是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的日记。在许多“大直男”看来,索菲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料理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让托尔斯泰在婚后写出了两部伟大作品《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夫妇两人对如何处理财产发生矛盾时,索菲亚就变成了落后的女人,等托尔斯泰年老、离家出走,索菲亚的形象就变成了“母老虎”,但波伏瓦提醒我们注意这个被大文豪遮蔽的女性,她的日记不是《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名著,但却记录了一个已婚女人的心路历程。索菲亚在新婚之后的日记中这样说,“我不断觉得我要死了。这很古怪,现在我有了一个丈夫。我听到他睡着了,我独自一人感到害怕。他不让我进入他的内心,这使我难过。所有这些肉体关系令人恶心。”在婚礼一年后,索菲亚这样说,“他老了,注意力太集中了。而我呢,如今我感到自己这样年轻,我那么想做出疯狂的事!我不但不想睡觉,我反而想单足旋转跳舞,但是,和谁呢?暮气沉沉的气氛笼罩着我,我周围的人都是年老的。我竭力压抑每一个青春的冲动。”等索菲亚经历了怀孕生子,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九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阶段,至于第十个月,最好不要谈。一切都完成了。我分娩了,我有过自己的痛苦,我振作起来,我带着恐惧和对孩子、尤其是对丈夫持续不断的不安逐渐回到生活中。我身上有某种东西破裂了。有一样东西对我说,我会持续地受苦,我相信,这是对不能完成家庭责任的担心。”波伏瓦分析说,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她说,索菲亚•托尔斯泰的歇斯底里是意味深长的,“大直男”会说索菲亚是个泼妇,一哭二闹三上吊,在她的日记里,她显得既不慷慨,也不真诚,我们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但她一生都通过不断的指责,在忍受做爱、怀孕、孤独以及丈夫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她没有武器,却有敌对的意愿,她以软弱无力的意志加以拒绝,假装自杀、假装逃跑、假装生病,对她周围的人来说,这都是可恶的,她几乎看不到别的出路,也没有任何积极的理由来压制自己的反抗情绪。 《第二性》第二卷,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写成长,第二部写处境,从结婚写到老年,第三部题为辩解,写恋爱的女人,写自恋的女人,第四部写独立的女人走向解放。波伏瓦时常以女字旁的“她”或者“她们”来展开叙述,很多时候,这个“女子旁”的叙述显现出了女性的整体困境,我们来看几句书中的原文——
她的整个生存是等待,因为她被关闭在内在性和偶然性的范围内,证明她生存的必要性总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她等待男人的敬意和赞同,等待爱情,等待丈夫和情人的感激和赞美,她等待他们给她存在的理由、价值和存在本身。
她的操心反映了对既定世界的怀疑。如果她觉得世界充满了危险,随时会陷入大灾大难,这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感到幸福。她不敢反抗,她不情愿地顺从。她的态度是持续的怨天尤人。她责备整个世界,因为它是在没有她,而且是为了反对她的情况下而建成的。
波伏瓦在这些叙述中时时展现出她的洞见,比如她写社交生活能让住宅成为一个迷人的领地,女主人可以借机展示财富,家中摆满转瞬即逝的鲜花,饭局成为一种神秘仪式。她写女人上了岁数,就可以用年龄为借口摆脱压在身上的苦差事,不再关心节食和美容,在夫妻关系获得领导权,也更愿意用嘲弄的语气说话了。波伏瓦用书中的这个“女子旁的她”,对各个年龄段的女性生活都做出了精准的描述,读者很容易从中获得共鸣,比如“女人头20年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她发现了世界,发现了自己的命运。她在20岁左右成为家庭主妇,此后便久久地受着丈夫和怀里孩子的束缚。”再比如,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这些动人的句子,会让读者感到,波伏瓦精准地写出了女人一生中的种种境况,“她责备整个世界,因为它是在没有她,而且是为了反对她的情况下而建成的”。波伏瓦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简单而言,存在主义哲学鼓励人们不断选择和创造,这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波伏瓦鼓励女性独立和解放,就是希望女人的超越性高于其内在性。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
 《永不妥协》剧照
《永不妥协》剧照  《黑天鹅》剧照
《黑天鹅》剧照  《性别之战》剧照
《性别之战》剧照 《杀死伊芙》剧照
《杀死伊芙》剧照


 《小妇人》剧照
《小妇人》剧照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妇女参政论者》剧照
《妇女参政论者》剧照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