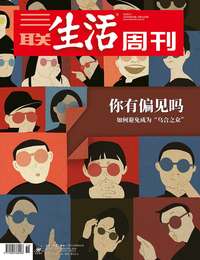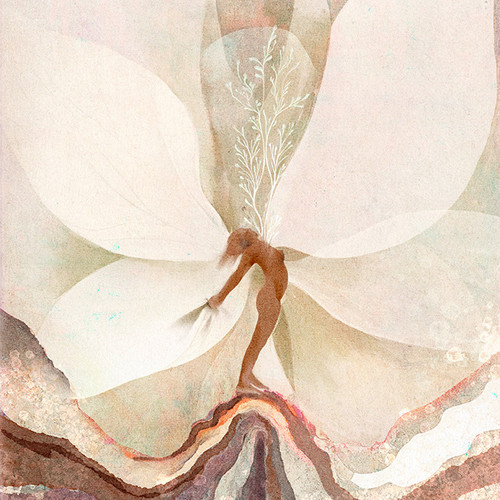莫言:小说有时候是会成长的,就像人会慢慢地成长一样
作者:孙若茜
2020-09-03·阅读时长2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1275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莫言(蔡小川 摄)
《晚熟的人》是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的第一本书。距离上一本,已经有10年之久。
它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里面的12个故事,基本都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的名字叫“莫言”,“我”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回到老家高密东北乡,发现并讲述的人和事。
莫言书写着,“莫言”又在被书写,被打量着。这样的讲述方式营造出了极为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常识告诉我们,“莫言”并不等于莫言本人,“他”的经历也并非纪实。我们在书里看到的那个“莫言”,站在当下,有他的迟疑,有他的谨慎和自嘲,也有他的有限和感叹。那么,“他”是不是莫言想要我们认识,或在诺奖之后重新认识的莫言?这有趣,但也许并不重要。更有趣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透过“莫言”对故乡人事的书写触及并透视这个时代。
在这本书出版后,莫言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为什么用这样的视角写作?那些从未被书写过的人物和形象,他们从哪儿来,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过去他书里那种西方油画式的表现手法如今变成了国画线条式的表现方式?诺奖带来的改变又怎样持续地发生着?
有风险,但我还是决定用这个视角来写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的印象里,你以往的短篇小说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孩子的视角,对童年、少年的家乡进行回望。但是在这本《晚熟的人》里,大都是一个得了诺奖之后的“莫言”的视角,也就是一种成年视角。对你来说,这两种不同视角,在写作上有什么差别吗?
莫言:的确是,我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童视角,也就是一个童年的、少年的我,立足于本地,没有外来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小说,像我上世纪80年代写的短篇《白狗秋千架》,那里边就是一个本地的青年到外面上了大学,在外面工作了,然后返乡的,(不过)他还年轻。《晚熟的人》基本是一个老人回乡的视角了,一个年过花甲的人回到故乡,头上还带着一个光环。
这么一个有一点名声的作家回到故乡,身份就很明确,会让读者一下子把小说的人物跟我本人画等号。这种预设实际上有它巨大的便利,也有很大的风险。它的好处就是会让读者容易把小说里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当作真正发生过的,好像纪实一样,无论我怎么写,大家都会认为是很真实的,就会造成一种现场感、真实感,会让人读得有趣味,我看看这个小子得奖以后回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阅读结果。
但我想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可能会让我老家的一些读者对号入座,那个晚熟的小子是谁?《红唇绿嘴》里面的这个女人又是谁呢?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但是对我来讲,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使用的视角。看起来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限制,实际上给我的是一个很大的自由,我想怎么写都可以了。即便我是完全虚构了一个故事,也有一种现场感,也有一种真实感。有风险,但我还是决定用这个视角来写。
这样的视角也会非常方便地把我在农村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全部调动起来,区别就在于,我过去写的那种“儿童小说”,就是一个儿童的眼睛所见所感知。现在我的视野肯定比儿童要开阔多了,我不仅有很丰富的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乡村记忆,也有了几十年在外面的生活经验,国际的、国内的。而且这几十年来,尽管在外地工作生活,但是我跟家乡的联系始终没有切断,尤其是现在交通如此之方便,真是到了抬腿就走转眼就到的便捷程度,所以每年回家很多次,对农村的变化发展,对村子里的一些情况,周围县市的情况还是了如指掌的。这样我写起来就是把我的家乡用我个人这样一个媒介,跟外地、跟世界勾连起来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而是一个以高密东北乡为原点往外辐射的故事。
文章作者


孙若茜
发表文章103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705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