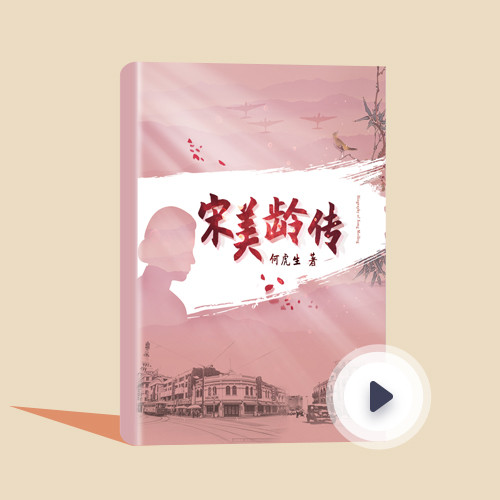真相拼图
作者:读书
2020-12-22·阅读时长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327个字,产生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邓子滨
常言道实事求是,可何谓 “实事 ”,无疑是首要难题。尤其在刑事治罪领域,特别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唯有弄清事实,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犯罪行为多数发生在过去,现场真相究竟是什么,需要一个还原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又非常容易出错。回溯性地重构一个案发现场,非常不同于认识并澄清 “这是一座桥还是一朵花 ”。
当然,能抓到现行犯是很幸运的,而所谓现行犯,不过是恰好有目击证人而已。没有目击证人的案件才是多数,这些案件需要串联其他诸多证据,形成完整的、闭环式的证据链,才能认定 “过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诸如事发突然或者与犯罪人并非同一种族等因素,都影响着对事的判断和对人的辨别,即使是当场目击者和被害者本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过去的犯罪真相难于查明,需要一场严肃的刑事诉讼对案情加以重构。这一过程非常类似考古,只能根据不断挖掘、打捞出的证据,像拼图一样逐步还原某个历史场景。拼图的意象将破案与考古勾连起来,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拼图越完整,就越接近真相,但实际上,一些拼片混乱无序,而另一些拼片则散逸难寻,从而干扰了拼图,甚至导向错误的拼接。而且,不是每个拼片都有同等价值,以人脸拼图为例,衣领、头发、胡须、额头的拼片再多,也不足以显现真面目,需要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缺失这些关键部位,比如抠掉双眼,便无从辨认,但若只剩两只眼睛,也让人无法识别。可见拼图的难题在于,拼片究竟多到何种程度才足以认定,少到何种地步便无复真相,简直不可言说。
拼图的比喻还有一个警醒功能:如果知道最后拼成什么样子,就更容易完成。正如在考古过程中对一座古墓的事先了解和预判,会影响对出土文物性质的认定一样,在刑事追诉中对犯罪真相的内心确信,会影响证据搜集和对证明力的判断,使侦查活动坚定地沿着预断方向进行,让证据及其链接为内心的既有结论服务,全不顾及辩护意见,以至于铸成覆盆之冤。在事先不知拼图全貌的情况下,拼图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余下的拼片可能并不唯一,选择往往不止一个。也就是,抽取拼片 A会呈现甲的面貌,抽取拼片 B会呈现乙的面貌。此时,侦查人员的个人欲望、情绪或者好恶都起很大作用,影响着案件走向,因为拼图不断扩大,真相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破案的冲动又让人欲罢不能,于是凭经验或直觉选择下一个拼片。
然而,拼图游戏可以不断试错,侦查活动却不能反复进行,一次选择就极有可能注定犯罪嫌疑人的未来命运。因此,刑事诉讼始于立案侦查,终于开庭审判,就是为了让后续每个诉讼阶段检验前一诉讼阶段,尽量减少人为因素。从侦查、起诉到审判,乃至上诉,每一步骤都应是障碍赛,而不应是接力赛,不能让后一程序沦为对前一程序的背书认可。
破案与考古的不同可能多于相似。考古没有时间限制,挖掘一旦无法持续,可以等待;而刑事程序则必须遵守法定期限,不能让案件在期限之外悬而不决,狱羁冤人,必须有一套对真相不明的疑难案件的处置规则。为文明诉讼所公认的规则,就是 “罪疑唯轻 ”“疑罪从无 ”。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