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重建平常建筑
作者:贾冬婷
2018-09-29·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441个字,产生8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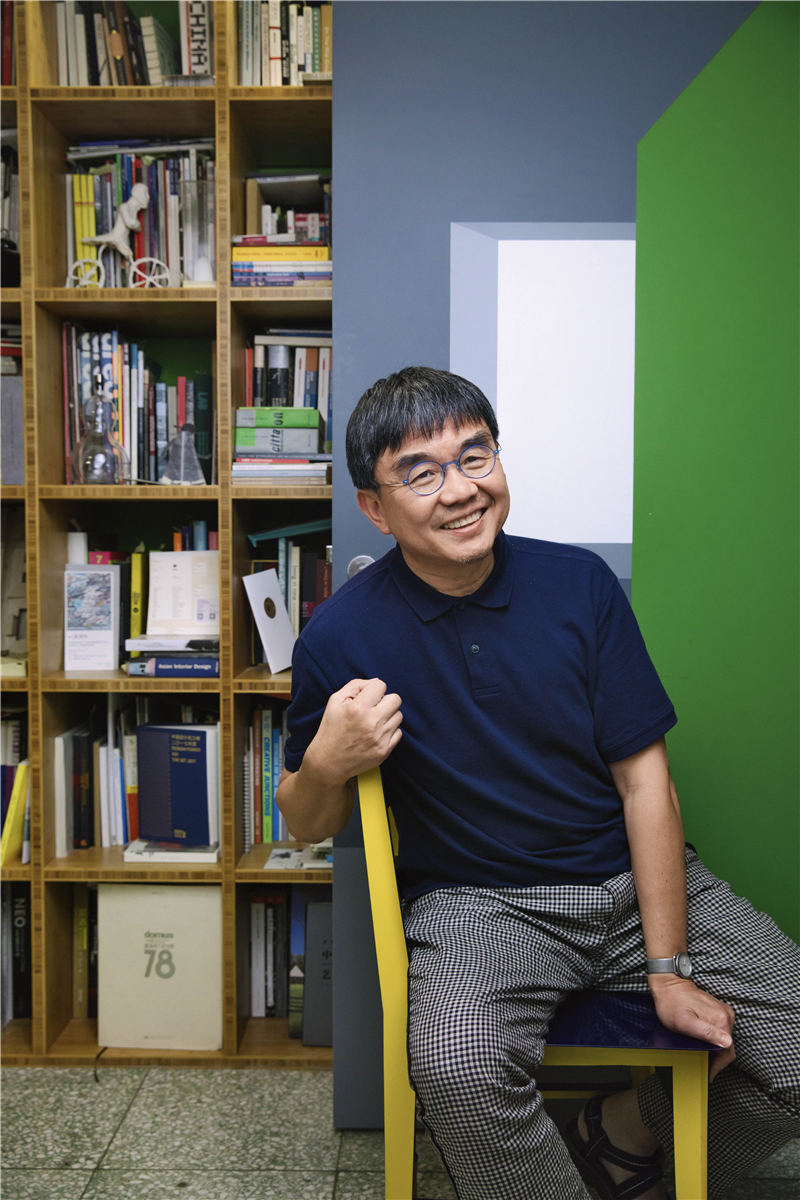
口述/张永和 采访、整理/贾冬婷
过去40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建筑领域的变化也不小,而且不止一次,我属于一个没落下的,都赶上了。
我父亲张开济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常常觉得,他非常疯狂。1967年,我们家被抄家,他也挨斗,但他却对我和我哥哥提出,“你们俩十来岁了,应该学英文了”,就去给我们找老师。到了第二年,有一天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出国,你敢不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机会上大学,更没有机会出国,可是我爸就会想这些,跟当时的外部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恢复高考之前的1976年,我还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工作,一次出差,从武汉坐船经长江去重庆,忽然听到船上大喇叭广播:“打倒四人帮了!”我对政治不大敏感,当时对将要来临的变化还没有明确意识,但对于以后要念书,因为我父亲,有一定精神准备。所以等到1977年能考大学了,我和我哥都没犹豫就考了。我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只读了三年没毕业,1980年后有机会出国了,我爸就极力怂恿。那时候出国的人还很少,私人护照的001号到004号我们也认识,是四兄弟,他们大概是1979年出去的,我哥是1980年,我是1981年。我可能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里面,学建筑的第一个。
我到了美国,跟现在留学去精英学校不一样,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后来我们就叫它“球大”。那是一个特别乡下的地方,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老玉米地,跟先锋的艺术、设计完全不沾边,我就在那里继续读完了本科。不过我这人有狗屎运,第二年就碰上一个老师,南非人罗德尼·普莱斯(Rodney Place),出身于英国建筑联盟学院(AA),他讲的都是文艺复兴时的绘画、雕塑、现代艺术,跟盖房子没多大关系,可是他对我后来成为建筑师的影响特别大。他的课,可以说是特别“禅”,就放一张照片或者一张古画,对着一屋子七八个人,问:“你看到了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不太会严肃对待,可他绝对不放弃。有次我实在烦了,把自己对一张画的理解讲给他听,他没反应;再问,他就说:“嗯,还有什么可能?”后来我在1985年又回到“球大”去教书的路上,开车在科罗拉多大山里,突然悟出来那张画的意思了,同时也不再关心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了。我的独立思考意识,也就从这么一个戏剧性的“顿悟”时刻开始了。我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师。
90年代中期前,我一直在美国教书,从“球大”,到密歇根大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到莱斯大学。后来就开始想盖房子。回国念头的萌发,我记得大概是在1988年,我去耶鲁大学看一个中国朋友,他说“我给你听点儿东西”,我们就去他的宿舍。那天下大雪,外头特别亮,他的宿舍里又黑又乱,他拿出一个录音机开始播放,音质糟透了,但音乐实在太震撼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没想到这么棒,于是开始想回中国,也就是奔着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去的。其实到今天也是,我觉得中国的机会除了所谓创业挣钱,还面临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催生阶段,建筑师也能在里面做点事情。
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开始得有点稀里糊涂。1993年我和鲁力佳回来过春节,有朋友找上门来找我们做设计,我本来也很想盖房子,就这么开始了,开始了就骑虎难下了。我后来得到去莱斯大学教书的机会,秋天到休斯敦,就想,注册一个公司吧!鲁力佳站在柜台上,要交7.5美金注册一名儿,我们没有名字就临时编,她说:“要不就叫‘非建筑’?”我比较实际,心想“要叫‘非建筑’,谁找咱们盖房子呀”!就加了个“常”字,叫“非常建筑”,用汉语拼音注册,觉得好像还有点儿意思,等于非常不严肃地干了一件严肃的事。我确实还有一层想法,就是觉得中国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过于怪异了。我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但实际上,满大街上的才真是非常建筑?
1996年我决定辞掉教职,回国当建筑师了。那时候,市场上还是以大设计院为主,只有几个零星的独立建筑事务所,独立建筑实践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再加上我们自己以前又没有真的实践过,所以那个艰难劲儿也超出想象。第一个真正建成的项目是席殊书屋,当时是在车公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楼里要建个书店,朋友介绍给我们。那个地方原本是过车的通道,只是那些年给堵起来了,我们顺着这个线索想到书店与城市的关系,把车流人流等要素汇合在一起,用现成的自行车轮子做了“书车”——一个旋转的书架。当时中国建筑界正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建筑师们都在谈论符号,实际上就是往建筑上贴装饰,我那时候意识到建筑学核心问题的缺失,席殊书屋这个小小的书店室内设计算是一种批判式回应,它在建成后收到的反响还是挺强烈的。尽管4年后被拆除了,原址重新又回复成了过道,但它对中国当代建筑学产生的影响大家还常常会提起,所以结果并不算“小”吧。
我到现在还在想,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建筑有没有白话文?现在的建筑设计实际上是文言文,因为有一种自我意识。我有时会有一种把设计做得直白的意愿,但回到中国实践之后发现,如果设计不明显或不张扬,业主会认为你没有设计,所以我一直想做出有说服力的“普通建筑”,但没做到。
文章作者


贾冬婷
发表文章79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1343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三联人文城市奖总策划。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