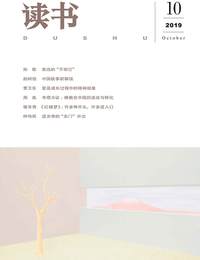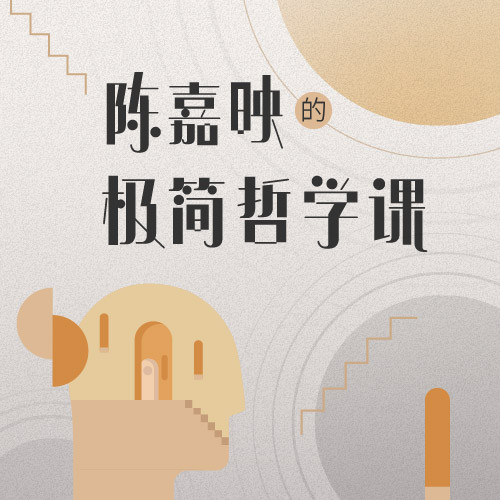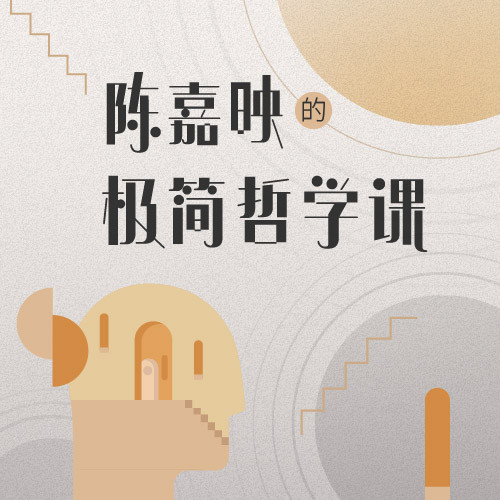躬稼与天下
作者:读书
2019-11-13·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859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董成龙
一
在《论语·微子》中,接舆、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这四个道家人士主张自然躬耕,对人为的政治世界发起批评(李长春:《政治生活:批评与辩护》)。农家的主张与道家的自然躬耕之论接近,儒家之中其实也有倾心于此论之人,譬如樊迟就曾表露心迹,其事见于《论语·子路》。
樊迟单刀直入,直接向孔子“请学稼”,又“请学为圃”,求问播种粮食或蔬菜瓜果的农事技艺(田园技艺),有弃文事农之嫌。樊迟问得直接,孔子答得也不含糊,直言不掌握这两种技艺,其实是指摘樊迟所问非人,终止问答。只在樊迟走后,孔子才更进一步,三次点出上有所好,下必有成:“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的事后点评才是真正的回答,这是说樊迟自以为在走治民的捷径,其实恰恰绕了路。君子之德风,若想治民,何必躬耕?显然这也暗中批评了“君民并耕”的农家主张。
儒者中倾心于农家的异数不只樊迟,陈相原本师从儒者陈良,听闻农家许行的学说后竟然“尽弃其学而学焉”,由儒学转向农学,这一点很像樊迟。陈相游至滕国,见到孟子后,更以许行之学与之论辩,以示弃暗投明。在他看来,滕国君主虽然是“贤君”,却“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君民若不能并耕,则势必造成在位者对耕农的盘剥蚕食,怎可谓贤君在上。
孟子反诘,如果依照一切自理的原则,要进食就要自行耕种,那是不是还要自己织布、织帽呢?陈相答曰,“百工之事”尽是专门的特殊技艺,工艺与农艺是两种技艺,人们做不到既“工”又“农”。孟子见此回答,不禁哑然失笑——难道“士”不也是一种特别的技艺吗?既然工匠不能兼事农耕,治天下的士人与君主就可以?
这里已经涉及士、农、工三民。孟子进而将人与事划分为两类,以期构成对人世的结构性理解:第一类是统治者(“治人”),他们是劳心之人,从事的是大人之事,因此“食于人”,由民人供养。第二类是被统治者(“治于人”),他们是劳力之人,从事的就是小人之事,因此“食人”,供养统治者。人分君野、事有大小,耕种与治天下不仅是两种职业,更是截然两端的志业,前者指向特殊的收益,后者担纲普遍的责任,“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所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孟子·尽心下》),治天下的大人若要一力担纲重任,怎会有闲暇躬耕?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