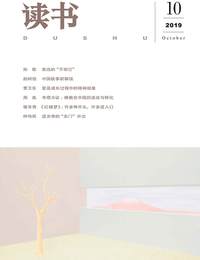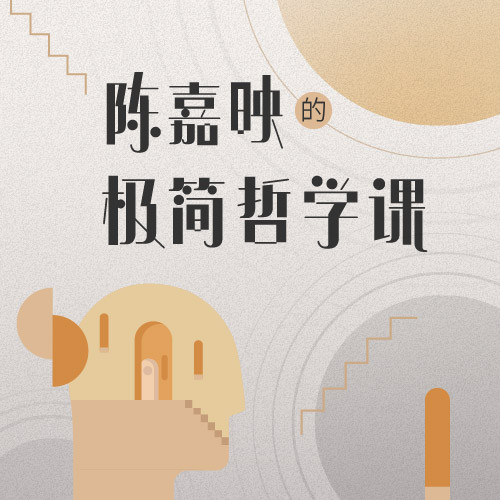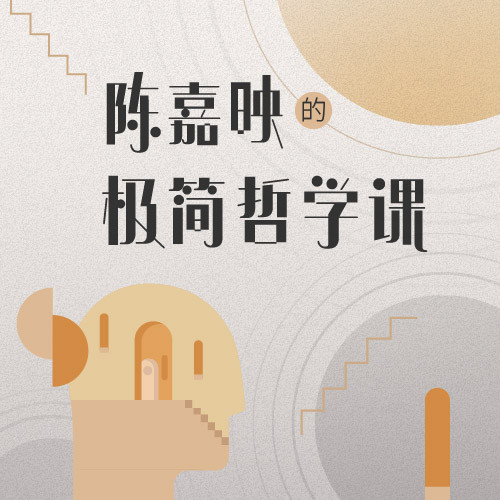帝国史中的辉格暗影
作者:读书
2019-11-13·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554个字,产生1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殷之光
让我们将时间向过往追溯一百年。
一九一九年,就在牛津贝特讲席(Beit Chair of C o l o n i a l H i s t o r y)开设之后十四年,剑桥维尔·哈莫史华慈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V e r e H a r m s w o r t h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罗德帝国史讲席教授(R h o d e 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也相继设立。这三个讲席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英国帝国史研究的“铁三角”,代表了帝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权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帝国史诞生于英帝国全球霸权秩序的顶峰。然而吊诡的是,在不足一代之内,这群英帝国史的权威们也目睹了英国乃至欧洲世界政治权威的衰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叙事被残酷的战争现实打击得支离破碎。
一九二九年,这批英国帝国史研究的主要学者们开始了一项持续近四十年的庞大工作——为“大英帝国”著史。这部八卷本《剑桥英帝国史》的首卷主编便是十年前开始担任剑桥维尔·哈莫史华慈讲席教授的约翰·霍兰德·罗斯,以及首位罗德讲席教授阿瑟·帕西维尔·牛顿。
就在开编之初,英国的全球秩序已经从“帝国”走向了“联邦共荣”。而到《剑桥英帝国史》第三卷“联邦共荣”于一九五九年出版时,这个英国苦心维护的全球贸易霸权秩序也遭到了更为严峻的打击。“联邦共荣”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设想也正在极速落幕。在“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苏伊士运河—这一连通欧洲与亚洲跨印度洋贸易线的核心关隘——被纳赛尔于一九五六年宣布收归埃及国有。而英国不惜一战的决心也未得到新崛起的“西方”—美国的支持。原本那些半独立的“委任”国家也在这股浪潮中,相继成为法律上的独立国家。
帝国史始终在追赶帝国政治兴衰的脚步。不过,“倒叙”仅仅表现了帝国史的一个侧面。在整个英国十九世纪全球霸权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于帝国发展顶峰时期的帝国史叙事,更展现了帝国全球秩序观及其道德叙事,与帝国实力政治本身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将一个知识、知识精英与帝国全球秩序扩张的政治历史关系展现在我们眼前。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