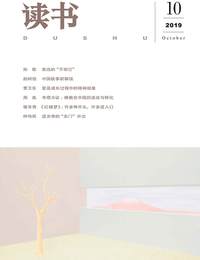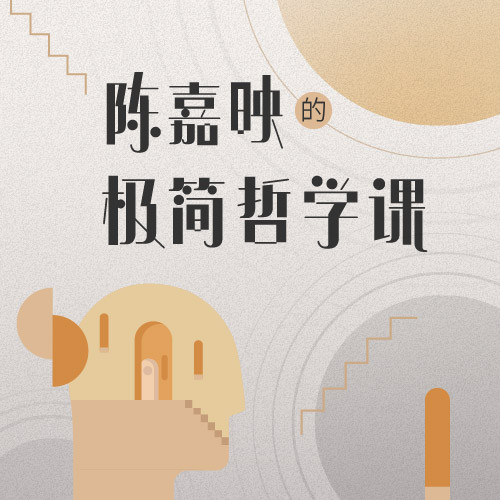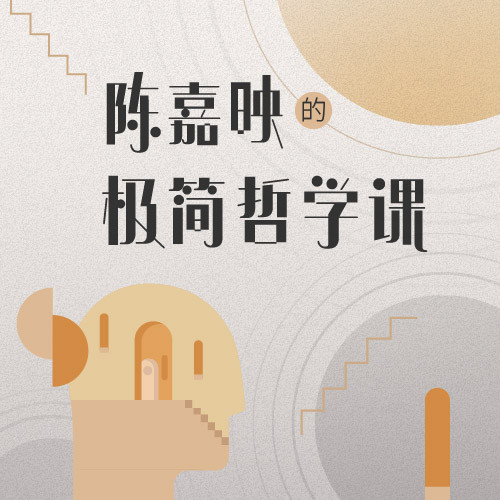荆轲刺秦王:幸好是插曲
作者:读书
2019-11-13·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334个字,产生7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裴登峰
在我国历史上,荆轲刺秦王,堪称大事,家喻户晓。人们言及荆轲,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燕太子丹率众宾客与其诀别的慷慨悲歌场面。《战国策·燕策三》这样描写: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夸张渲染,甚至演绎出了带有荒诞色彩的故事。司马迁曾感慨:“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荆轲论》五篇”。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其文已佚。后来吟咏其人其事,成为历代文学作品中的题材。人们大多持欣赏、肯定态度。对荆轲未完成刺秦“惊天伟业”,心存遗憾,感慨良多。荆轲也被涂抹了“悲情英雄”色彩,成了壮志未酬的“遗憾者”的代名词。
但事实上,荆轲是被“逼”出来的豪杰,其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战国三大刺客,豫让为了报答“知伯以国士遇臣”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刺杀赵襄子,体现“士为知己者死”的执着信念。聂政深感“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他为了回报韩国权臣严遂“看得起自己”的厚遇,觉得“应该”去刺杀韩傀。虽是被严遂利用,无关乎“正义”,但聂政却是出于自愿。豫让与聂政,都体现着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荆轲的行为动机,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起初,荆轲由卫至燕,“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后来好友田光告诉他,已在燕太子丹面前,举荐他去“图国事”。在田光自杀以激将后,“荆轲遂见太子”。虽然“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苦劝,但荆轲开始并不情愿,不为所动。“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于是,“太子丹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这实际上是强人所难,强加于人,非荆轲本意。即便如此,“久之,荆轲未有行意”。面对一再催促,“荆轲怒叱太子曰:‘……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诀矣!’遂发”。荆轲明知此去必死,但若不去,太子丹也不会放过他。两者结果相同,索性不如刺秦王而死。荆轲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身不由己才去刺秦王。谈不上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并非充满豪情、义无反顾的“义士”或“高大”英雄。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许多地方或以简短议论,或以叙述甚至抒情口吻,表明态度。有时一字含褒贬。在《史记·王翦列传》里言:“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用一“贼”字,或许表明着情感色彩。《资治通鉴》删去了易水送别场面,可能表明了司马光并不称道的态度。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