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之前:“西潮”与“后土”之间
作者:艾江涛
2017-12-27·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452个字,产生6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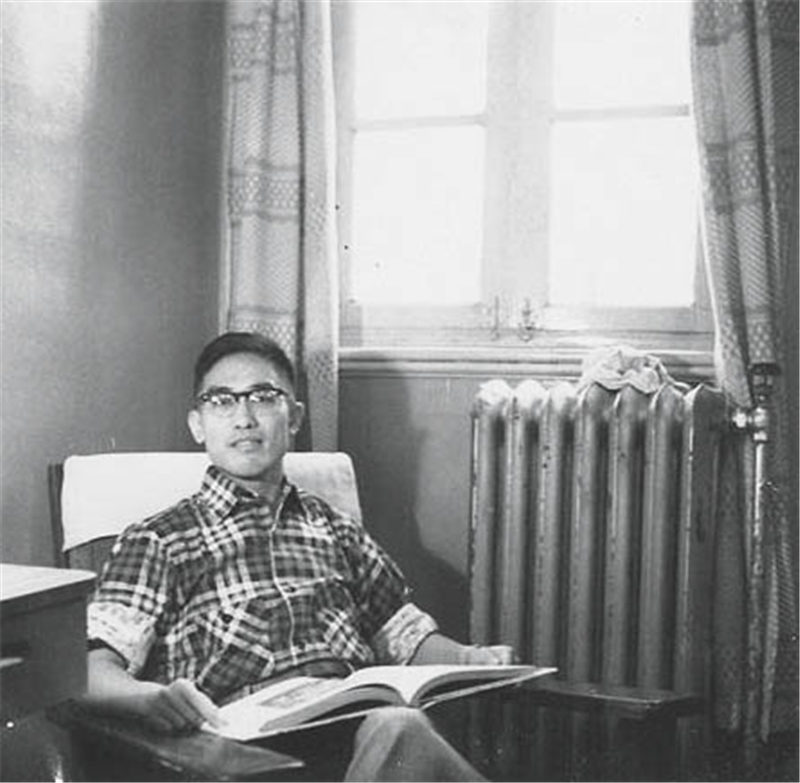
“后土”难离
1949年春,为了躲避内战的战火,金陵大学外文系大二学生余光中,不得不转学到厦门大学。几个月后,他跟随家庭辗转香港避难。这样的逃难经历甚至路线,对21岁的余光中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底,南京陷落日寇之前,余光中便跟随母亲逃回常州外婆家,随后一路迂回到上海法租界,在那里渡过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在1939年夏天经香港、越南,历经艰辛,才到重庆与父亲团聚。
不同于还能在厦门大学插班就读,香港一年是在无学可上的苦闷中渡过的。1962年,刚刚在台湾获得年度“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的余光中,应《自由青年》杂志之邀撰文自述写诗经过,回忆起那段日子:“面临空前的大动乱,生活在港币悲哀的音乐里,我无诗。我常去红色书店里翻阅大陆出版的小册子,我觉得那些作品固然热闹,但离艺术的世界太远了。我失望,我幻灭。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台湾海峡的两岸,作一抉择。而最苦恼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劝我回大陆,不久她自己真这样做了。我没有去。最后我踏上来基隆的海船。那是1950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隔着十多年的时光,当初的赴台成了更多出于艺术考虑的某种抉择。只是,余光中没有想到1949年夏天于甲板上回望的那片大陆,从此犹在梦中,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而在梦的彼端,则是二十多年在华山夏水中度过的日子与点滴记忆。写诗,用余光中日后的话来说,如同叫魂与祷告。
但在20多岁离开大陆,而不是更年轻,对他来说则是一种幸运。2002年,74岁的诗翁余光中,在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序言中写道:“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显然,这块被他称为“后土”的大陆,已为日后的诗人打下最初的积淀。
在国民政府侨委会任职的父亲余超英,本身具有相当古文水平,一有机会便为余光中阅读讲解《东莱博议》《古文观止》中的道德文章。1939年,余光中在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就读,曾做过小学校长的远房舅舅孙有孚也逃难到附近,并带来大量藏书,这些线装本古籍很自然地为他打开古典文学的大门。初三之后,国文老师换了一位前清拔贡戴伯琼,在他的指点下,余光中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从而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而早在上海法租界时,余光中便有幸接触到英文,在中学他又遇到出身金陵大学的英文老师孙良骥,高一便崭露头角,一举夺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语演讲第三名。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到出生地南京。1947年,余光中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其时内战的硝烟已经蔓延北方,在母亲的劝阻下,他最终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
刚读大学时,尽管班上已有几位同学在热烈地写着新诗,但余光中颇看不惯他们那种诗意淡漠的分行散文,他最初的兴趣还在五七言古诗之中。后来接触到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诗集《凤凰》还有新月派诗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又在一本批评文集《诗的艺术》中读到卞之琳和冯至的诗歌,再加上对英国浪漫诗人及惠特曼的原文阅读,余光中开始写作新诗了。多少有些幸运的是,在厦门大学的短短数月内,他竟在当地报纸副刊接连发表了六七首诗作。
这种幸运一度延续到渡海之后的台大时期。一次,同班同学蔡绍班擅自将余光中写作的一叠诗稿拿给梁实秋看,没想到余光中不久便收到梁的一封鼓励有加的回信,后者自此也成为他在文学上最重要的引路人。1952年,即将毕业的余光中出版首部诗集《舟子的悲歌》,不出意外,梁实秋不但为他写了序言,还亲自撰写书评称“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
尽管处女诗集没有带来幻想中的轰动,但已足以使余光中成为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据台湾诗歌史研究者刘正伟讲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空气紧张、文化寥落的台湾,能够出诗集的人很少,某种程度上,也正因此,比他年长十几岁、有台湾现代“诗坛三老”之称的覃子豪、钟鼎文(另外一位为纪弦)后来才会亲自找上门来,拉他共组蓝星诗社。
文章作者


艾江涛
发表文章131篇 获得5个推荐 粉丝626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