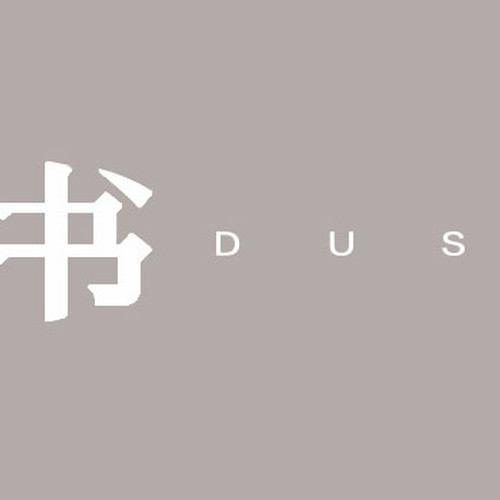怀念杨新:漫长友情中的三个时段
作者:巫鸿
2021-02-18·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663个字,产生1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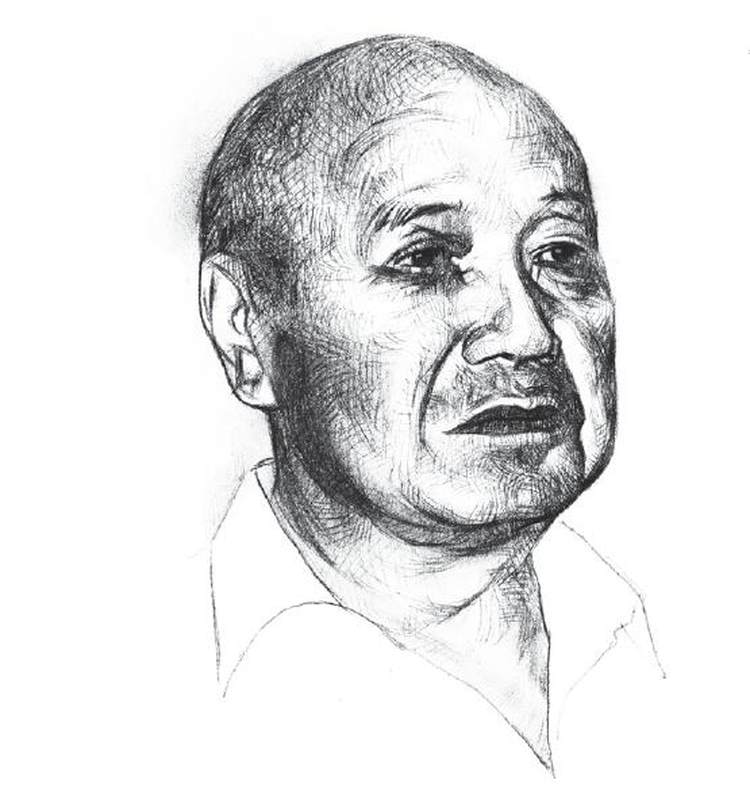
杨新像。李有良绘
杨新走了。这以前就听说他的身体不好,去年回国时想去探望,但诸事繁多未能成行。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总觉得他就在那里,见不见都是老朋友,此次不见下次还可以见。但他真的就走了。
我说 “几十年 ”并非虚词——我们首次见面是在五十七年前的一九六三年,当时他作为美术史系的学长之一,在校门口欢迎我们这班刚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那年由于政治原因,美术史系之外的系都不招生,我们这班的十个人因此也就是学院新生的全部。美术史系在美院中算是新创之系,当时只有三届:杨新在最高一届,我们是最低一届,中间还有院校调整转过来的一届。我们班是 “文革 ”前美院招收的最后一届本科生,杨新他们却在 “文革 ”之前就已毕业分配,因此重叠时间不长。记得他个子矮小但神采奕奕,讲起话来带着湖南口音。听同学说他爱画画,也画得不错,这使我感到和他较为亲近。有一次他到我们班的绘画教室来串门,我们刚完成的人物写生还立在画架上。他一张张仔细看过去,像是参观一个展览,时不时赞上两句。少有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种小事在我和他相处的过程里有很多,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时间一长,大都也就忘却了。突然跃入脑海的另一瞬间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时我已经去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杨新那年也作为卢斯基金会访问学者,受高居翰邀请去加州伯克利大学访学一年。初夏,我正好得到一笔基金会资助,去美国西海岸参观美术馆并会见同行学人。从西雅图一路开车到伯克利,见到杨新非常高兴,二人彻夜长谈,从这些年的故宫情况到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当然也有个人的经历。第二天高居翰兴冲冲地召请我们和他的学生去海边游玩。海水极冷,我们两人是 “唯二 ”的下海勇敢分子。进入水中没有几分钟,旁边 “咕嘟 ”冒出一只海狮的圆头,把我们吓回到岸上。
一九六三到一九八四年之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世界历史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对于我和杨新来说,最大的事就是我们被命运抛在一起,在“文革 ”中和 “文革”后的几年间成为 “一纸之隔 ”的两家邻居——这是标题中所说 “三个时段 ”中的第一个。我们的住处是故宫博物院里称作 “十三排 ”的一溜儿小院中的一个,灰墙灰瓦,紧挨着紫禁城的高大东墙。人们都认为紫禁城多么宽敞,很少注意到它的边边角角。“十三排 ”和它旁边的小巷就属于这类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嵌在紫禁城双层高墙之间的一条狭窄空间里,西边是内宫的红墙,东边是外城的灰墙。每个小院有面阔三间的南房和北房,除了正午一段,大多时间都隐蔽在两边城墙投下的阴影之中。
文章作者


巫鸿
发表文章36篇 获得7个推荐 粉丝1085人
著名艺术史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东亚艺术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