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带给今日世界的信息
作者:薛巍
2022-03-29·阅读时长7分钟

2021年6月,朱利安·巴恩斯、汤姆·斯托帕等上百位文化名人给英国遗产委员会写了一封联名信,要求像对待其他英国作家的故居那样,给茨威格在伦敦的故居也钉上蓝色的标识。起因是2012年,英国遗产委员会拒绝这么做,理由是“茨威格跟伦敦的关联不够强,他在英国也不是很出名”。
联名信中说,英国遗产委员会的理由令人不解,“普希金等出版社出版的新译本已经让茨威格成了英国读者熟知的作家。1933年他在波特兰宫租了一间公寓。那时他在英国确实不如他在欧洲大陆著名:伦敦给了他图书馆、匿名性和思考自己想做什么的空间。他来英国本来是为了写一本关于伊拉斯谟的书。茨威格称伊拉斯谟是第一个自觉的欧洲人。他撰写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致力于用希望反制大众迷醉的时代。在他的人生、在欧洲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波特兰宫11号,来完成他对伊拉斯谟和他的泛人类理想的辩护,这值得让更多人知晓”。
去年1月,《新政治家》刊发的一篇文章说,在疫情蔓延、边境关闭的时候,人们又开始读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过去10年间,欧洲人把《昨日的世界》当作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时期的生存指南。如今,特别让人心有戚戚的是茨威格对惬意的都市生活的怀念。“在诺伦多夫广场旁的一家咖啡馆二楼,每周举行一次聚会。各式各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有诗人、建筑师、扮风雅的文人学士、记者,还有扮作工艺美术家和雕刻家的年轻姑娘、想提高德语水平的俄国大学生和满头淡黄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女郎。大家聚集一堂,展开激烈的争论,但不受任何拘束。有时朗诵几首诗或剧本的片断,但对所有人来说,主要目的是在此彼此结识。”他认为要求使用护照是不开化的,边境的盘问和搜查有辱人格。他无疑会认为今天谈论的疫苗护照、隔离酒店、旅行走廊让人感到沮丧。

2015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在给茨威格文集《失落世界的信息》作序时说:“今天,茨威格之所以是一位必要的作家,是因为他的欧洲观。他体现了20世纪欧洲心灵中的一些核心矛盾:信奉高度的理想主义,又感到文明很脆弱。他相信欧洲可以不再是一个就民族和种族争吵的大陆。但他依恋过去安稳的世界,不相信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模式来重建社会,也不相信自由主义文明能够获得新生。过于信奉世界主义理想,导致他没有注意到这些理想已经受到了挑战。茨威格对欧洲的怀疑更加紧迫,尤其在今天的欧洲,民族主义复苏,欧洲的机构不知如何应对前来寻求安全的难民,他的怀疑和担忧仍跟以往一样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有些人认为茨威格是二流作家,但2007年,评论家克莱夫·詹姆斯在《文化失忆》中为他辩护说:“茨威格精通多种语言,举止完美,全球闻名。他积累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无论是以散文还是专著形式,仍然是令人几乎无法仰视的成就。茨威格是他欣赏的一切的总和,他的风格赋予他们在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精神上的统一。他的笔调大都富有诗意,简单说来就是拥有诗句那种具体而微的生动性。茨威格对蒙田的描述总是很精彩,他拥有与蒙田同样的概述和评价历史人物行为的天赋。茨威格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manofletters):也就是说,他无法做任何其他人。‘二战’之初他说‘我们的世界毁了’,指的是每一个为艺术、为学术、为人文主义而活着的人。”
2014年,乔治·普罗契尼克出版《最后的放逐:世界尽头的茨威格》,书中说茨威格是一个“富有的奥地利公民、无休止地漫游的犹太人、极其高产的作家、不知疲倦的泛欧洲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不间断的人际网络建立者、无可挑剔的主人、高尚的和平主义者、谨慎的感官主义者、爱狗者、恨猫的人、图书收藏家、穿鳄鱼皮皮鞋的人、花花公子、抑郁症患者、咖啡爱好者、孤独心灵的同情者、漫不经心地玩弄女性、朝男子抛媚眼、奉承当权者、捍卫无权者……”
《纽约时报》影评人A.O.司科特在书评中说:“在欧洲大部分地方,茨威格仍然是一个人们熟悉的、流行的人物:一个和蔼可亲、兼收并蓄、大大方方的小作家,当那些更加威严的大作家如托马斯·曼让人感到疲惫的时候,他很容易被人接受。《昨日的世界》让茨威格成了一种怀旧之情的代表。托马斯·曼、汉娜·阿伦特和布莱希特等德语作家把生存变成了一种反抗形式。面对道德和政治灾难时,他们很坚决地向明日的世界迈进。而60岁的茨威格认为自己属于过去。他决定待在那里,他还处于那种享乐主义的精致和知识热情氛围中,在一个已经消失的城市的咖啡馆出没,在它的大街上漫步。茨威格现在尤其吸引人,因为他不是宏大思想的创始人,而是一个严肃的表演者,一位热情、仔细地观察习惯、激情、怪癖、错误的人。”
2019年,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评论了茨威格小说和《昨日的世界》的英译本。“在《与魔鬼搏斗》中,茨威格说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都没有妻子儿女,没有房子和财产,都没有长期的工作和稳定的职务。他们的友谊脆弱易碎,他们的地位丧失殆尽,他们的作品没带来收入:他们永远处于虚空之中,在虚空中创作。茨威格在这里描写的是他1942年前的生活的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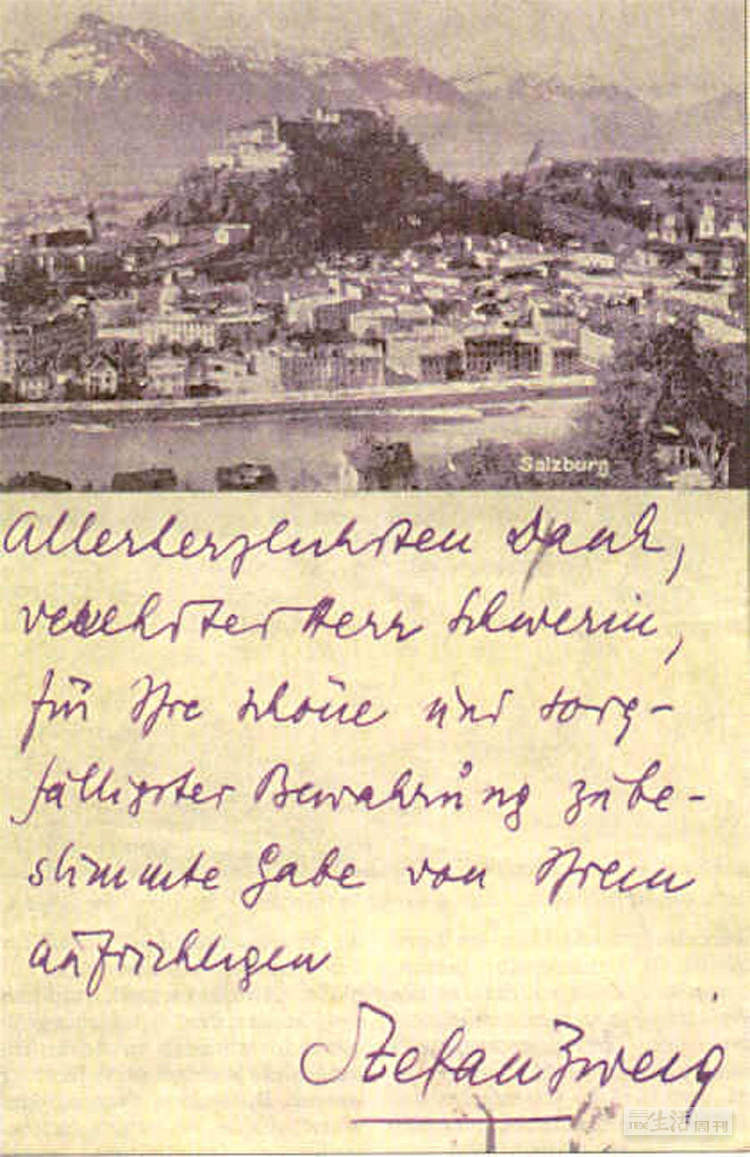
茨威格的小说和传记全球畅销,他是一位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都毫不拘束,能用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发表演讲。1938年,有2400人听他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讲“艺术创作的秘密”。他给理查德·施特劳斯写剧本。他的朋友和熟人包括里尔克、罗丹、弗洛伊德、高尔基、罗曼·罗兰。
爱泼斯坦说,茨威格的小说中充满洞见和格言,如《一颗心的沦亡》中说:“认识自己就是维护自己,但通常都是徒劳。”《心灵的焦灼》中说:“唯独受到命运亏待的人,唯有那些六神无主、遭人鄙视、丧失信心、相貌丑陋、受尽屈辱的人,才能借由爱情获得帮助。将自己的人生献给他们,也就弥补了生命从他们身上夺走的东西。只有他们懂得爱与被爱,知道如何去爱,那就是心怀感激,谦卑恭顺。”
《感情的混乱》中写一个学生迷上了老师,茨威格用一段杰出的关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人的讲座来解释这种迷恋,让读者也着了迷:“在大洋彼岸,新的机遇蓬勃发展起来,世界变得辽阔广袤,人的心灵也伸展开来,要和世界一样——人的心灵也要扩大,它也要在善恶两方面都趋于极端;它要发现,占领,像那些征服者一样,它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力量。于是一夜之间用这种语言说话的人,诗人,便应运而生,十年之内涌现出五十个、一百个诗人,都是些狂放不羁、桀骜不驯的家伙。”
在《象棋的故事》中茨威格对象棋做了最好的描述:“象棋这种游戏既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颖的;其基础是机械的,但只有靠想象力才能使之发挥作用;它被呆板的几何空间所限制,而同时它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它是不断发展的,可又完全是没有成果的;它是没有结果的思想,没有答案的数学,没有作品的艺术,没有物质的建筑。”
尼采最吸引茨威格的地方在于他的预言能力,“没有人像尼采一样感觉到了欧洲社会大厦的摇摇欲坠,没有人曾以这种气象学的准确预感到我们这场将临的文化灾变的一切细节乃至它的威力。他已看到了危机的根源在于为了造成目前欧洲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离而产生的民族猜忌心理和血液中毒与愚蠢的民族主义”。
2012年,《纽约客》编辑里奥·卡里说,新的茨威格传记《三种人生》显示,茨威格并不是他想成为的道德权威,他其实比人们以为的更加活跃,也更具有普遍的人性,他最好的作品都源自他的脆弱,而不是他高贵的志向。传记挖掘了他年轻时的日记,发现他非传统的性探险。
卡里说,茨威格写得最好的作品包括他的短篇传记散文,展现了他勾画人类生活模式的能力,比如他写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开头用一页半的篇幅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行迹:“在德国,没有哪个方向是这个不安宁的人没有踏上过的,没有哪个城市是这个永远无家的人没栖居过的。滚滚不停的车轮载着他经过米兰和意大利沿海又前往巴黎……从德累斯顿出发,途经奥地利战场,冲向维也纳。在阿斯佩恩附近的战役中,他被逮捕,后来逃往布拉格。有时他一连几个月像一条地下河一样消失不见,然后在几千里以外重现。他是迅疾地飞离绷紧的弓,飞离自己。他调换城市就像热病病人调换枕头……到最后,重力把这个被追逐者抛回了柏林……在万湖,他将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头颅。他的坟墓坐落在一条乡村路旁。”这一密集的文字盛宴再现了克莱斯特的一生,证明即使是最动荡、模糊的情绪,从外面观察,也能看出其固定的模式。茨威格的漫游也可以列出这样一个清单:苏黎世、伦敦、巴斯、莫斯科、里约。“在职业生涯的顶峰时期,茨威格是人们敬仰、嫉妒、俯就甚至蔑视的对象。他经常解读他人的生活,从中寻找教训。他自己的人生也成了一个关于艺术家的命运的警世故事。”
文章作者


薛巍
发表文章569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4698人
江湖人称“贝小戎”、“小贝”,读书万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