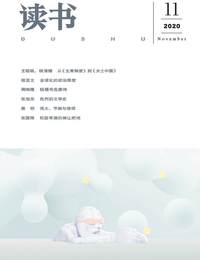全球化的政治限度
作者:读书
2020-11-27·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674个字,产生2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程亚文
在谈论全球化时,人们往往会把它说成是一种经济过程,即所谓“经济全球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如此定义:“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在这些描述中,全球化是中性的,仅仅是一种经济过程,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好像没有多大关系。相当长时间内,全球化在西方政治家的演讲和谈话中,也一直是一个饱含积极、正面意义的词语,被说成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代表着人类文明走向。
然而,对全球化的显著不满,近些年来出人意料地来自发达国家,这在提醒人们,以往对全球化的一些美好想象,可能是对全球化的性质缺乏足够了解,而它主要又缘于对全球化从何起始及其本原体认不足。《读书》二○二○年第二期汪毅霖先生的文章《“逆全球化 ”的历史与逻辑》认为,“逆全球化 ”现象主要来源于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两种诉求之间存在内在紧张。这个解读是说得通的,但意犹未尽之处在于,将全球化过多与 “自由贸易 ”挂钩,仍有把全球化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且从结果和过程来理解全球化造成的 “内在紧张 ”之嫌。我们还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深入探析全球化的初始发心与动力机制,以及从资本与政治的国际国内互动和相关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更好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乖张。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是对此有精致思考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全球化 “仅仅是社会权力资源扩张的结果 ”,而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则“意味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意味着民族 —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 —开始具有两个帝国,后来则只剩下一个 ”。也就是说,全球化是曼所说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四种权力运动的结果,在后者的驱动下,资本主义、民族 —国家和帝国这三种宏观制度的建构与展开,是为了进一步拓展这四种权力。全球化在其展开时,是有主从关系的,由于四种权力的优势方主要是在少数大国手中,它们也就成为主动方,在一九四五年之际是美国和苏联,而在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唯有美国。全球化远不只是在商业动机驱动下市场的全球整合,而是各种社会群体谋求扩张其集体权力和分配权力以实现其目标的结果。美国在 “二战 ”结束后主动帮助欧洲原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后来接受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都是同一逻辑在不同时期的类似演绎,这也是过去一些年间 “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这一话语的由来,以及全球化和 “二战 ”后国际秩序的实质所在。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1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