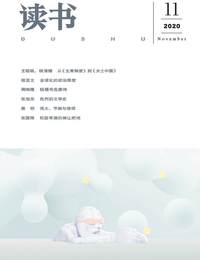批判的文学史
作者:读书
2020-11-27·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271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张旭东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分工,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和公共讨论中的热点,也是最活跃的表达方式之一,其影响和辐射远远超过狭义的专业范围本身。随着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领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学议题则相对边缘化。伴随大学文学教育的学科专业化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逐渐失去其公共性、思想性,而更多地成为一个知识 “领域 ”。
其中 “文学史 ”作为我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范式和知识传承方式,本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其知识生产方式和训练体系既有历史合理性,也有历史局限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知识分子写作 ”的一个基本样式,从个人情感、群体心理到伦理冲突、社会矛盾、政治改革甚至经济发展,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写作方式统统可以 “介入 ”,仿佛文学的边界、思想的边界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边界。这个理想的阶段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如今更多是作为怀旧的话题被人谈起,但其实在近代不乏先例。从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学式和批评式写作(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德国浪漫派文学批评(施莱格尔兄弟、海涅),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执民族思想生活之牛耳、引领民族精神生活的风气和中心话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种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以自身的创造性、迫切性和重大议题,一马当先地走在了 “文学史 ”的前面,界定了日后文学史写作的材料、框架和内在理路。作为一个特例,从白话革命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文化思想历程,则是通过 “新文学 ”先驱和后继实践者自觉的文学史编纂和经典化努力,同时通过左翼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艰苦探索和积累,最终以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础 ”的形式确立下来。这种工作虽然在 “文学史 ”框架下取得了最为具体的成果,但就其参与者群体自身的文学经验、审美判断力、知识理论抱负乃至政治自觉而言,根本上讲仍然是思想性的、批判的、创造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批评和研究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性和当代性,使得现代文学学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模板。这样看,随着专业建制内去思想化、反理论和非政治化倾向的发展,现代文学 “二级学科 ”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学科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甚至用以 “安身立命 ”的文学史范式本身也往往需要向文学以外的领域(学术史、思想史、印刷文化、物质文化等)求助,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回顾那些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特殊瞬间,可以看到它们都像闪电照亮夜空般昭示了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以及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内在动机。比如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应该归属 “审美鉴赏 ”(康德所谓的 “判断力 ”)范畴,还是认知、分析和理解(康德所谓的 “纯粹理性 ”)范畴?就其非功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言,或者说在感官、想象、形式和风格的自律或自由中暗合了必然和规律而言,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需要一种同它的本质相适应的体验方式和感受方式。这是作为美学或艺术哲学的文学鉴赏。与此同时,文学和艺术一样,又是一种复杂现象和复杂结构,包含了高度构思和提炼的人类精神劳动,因此需要一种专门的、经过长期训练的知识、理论、经验、方法、技能,方能被全面深入系统地把握。这就是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包括实证层面、形式分析层面、文学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层面。不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活动范围,仍然大大越出了这两个人类官能范畴。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