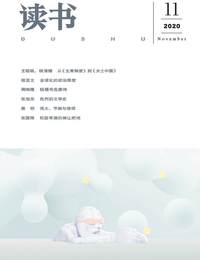替谁树碑,为何著史?
作者:读书
2020-11-27·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290个字,产生1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盛 洪
茨威格善写传记。他选择的传主却不同一般。这些传主功勋卓著,声名却不显赫。当然,这是与更为著名的那些人相比。例如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茨威格写了西方世界发现太平洋的第一人,巴斯科·巴尔沃亚,他因是逃犯,被嫉妒者借机处死。结果他的名字被湮没在历史中,而杀他的皮萨罗却暴得大名。另一个人是英国的北极探险队长斯科特,他在 “到达北极第一人 ”的竞争中输给了挪威队,本人也死于这次探险,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不少史家皆有此倾向。如司马迁写《史记》,《列传》第一篇就是《伯夷列传》。为何是伯夷?他与叔齐因竞相辞让君位而逃到周,正碰上武王伐纣,他们认为是不孝不忠,于是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孔子赞他们节操高尚,然却饿死;太史公为他们抱不平:“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道似不公。“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史迁为他们树碑,又是以史家的努力还他们以公道。这也包含了这样的深意,一个文明的道德价值不仅在那些成功和胜利的人身上闪光,也在看来失败的人身上遗存。后者是这一文明必要的补充。在历史中丢掉这两个人,丢掉这种精神价值,中华文明就不完整。
到现代,有陈寅恪先生著《柳如是别传》。一般看法,柳如是只是明末一歌妓,是陈寅恪在那一时期的无奈选题。然而柳如是却非一般女子,不仅在于她与陈子龙和钱谦益的两段恋情,而且她自身就有独立之价值,这在妇人身上尤为醒目。人们常引陈寅恪之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尤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忽略紧接着的后面这句,“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五年版,4页)实际上前句是为后句的强调做铺垫。这种忽略恰是陈寅恪想加以扭转的事情。于是他在散乱文献和故纸残片中重新拼起一个真实的柳如是,以补丧失士大夫精神的当代知识分子之缺。
茨威格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也是如此。他明确地说:“我从不愿意为那些所谓 ‘英雄人物 ’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的悲情。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保持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336页)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马丁·路德,因为世界史课本必有他的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伊拉斯谟的名字。我自己也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一本题为《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的书,不知作者伊拉斯谟何许人也,读了几页,就接着读了下去,竟把它读完了。
在不少 “现代人 ”看来,君主还需要教育吗,目的是什么,难道还要教育出一个圣君来吗?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民主制度啊。然而,不要说伊拉斯谟的时代欧洲大陆还是以君主制为主,英国也还处于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时期;即使是在现代,把“君主 ”换成 “民选总统”,这本书仍有它的价值,因为民选总统也需要道德约束。当然,伊拉斯谟知道暂时无法投票选择君主,所以他说:“要是无权选择君主,就必须相当细致地挑选教育王储的人。”这很重要。伊拉斯谟说: “对于生来就享有广土众民甚至主掌世界的而非三两村舍的人,他要么成就良质,造福万民,要么沦为恶徒,祸害苍生,我们殚精竭虑于如何教养他,又是何其正确。”
怎么教育,用什么教育?伊拉斯谟已在书名上点明,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构成西方文明的两希文明之一,显然扮演着侧重精神价值的作用。虽然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组织在相当长时间里有着实际的司法管辖权,强制性征收十一税,还经常凌驾政府权力或至少与之抗衡,但在历史中逐渐演变为一种超世脱俗的精神资源。因而,要用基督教来教育君主。这样看来与儒家有几分相似。儒家虽然也为政治结构的有形制度提供了资源,如三省六部制、谏议制度、科举制度和史官制度等,但儒家还是强调对君主的教育,即朱熹所谓 “正君心 ”。正君心就是 “格君心之非 ”。孟子曾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就是说贤德博学之士能够矫正政治领导人心中的错误,就是要由儒家士大夫来教育君主。
中国自西周开始就有太师、太傅之职,其职能之一,就是作为君主或太子的老师。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周公就是中国第一任太傅,他的学生就是周成王。即使王储登基或幼帝成年亲政,这一教育也不会中止。还有经筵讲席制度,君主定期上课。太傅或皇帝老师大多是当朝大儒。如强调 “正君心 ”的朱熹就当过宋宁宗赵扩的讲官。到了清代这一制度更为完善,并有详细记录。《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康熙皇帝每次听讲的时间和地点、讲官和内容。
抽象地说,人类结成社会或政治体,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为了有效操作,需要由具体个体来代表这个政治体,这个人即所谓 “君主”。理论上的君主行为应符合社会最大福利,但具体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个人。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向来有两种倾向:一是哲学王的倾向,即选择哲学家来担任君主;一是需要用外在制度来制约君主。到了现代,随着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似乎是后一种倾向占了上风,并且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前者则被忽视和抛弃。然而,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功都不是单一制度决定的,而是由多种制度安排组合而成的 “制度结构 ”起的作用。简单地说,制度结构至少包含两个方面,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有形制度是可以用文字描述,不排除用强制性手段实施的制度;而无形制度是内化于人心,通过人的自律产生作用的制度。但后者即使起作用,也往往不引人注目。于是宪政民主的成功就看起来归功于外在制衡的制度了。
其实,仔细看一下历史,哪怕只是西方历史,就可以知道无形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罗马皇帝都是不可一世之人,但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据爱德华·吉本,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以后,就变得极为谦恭。在一次宗教大会上,“君士坦丁耐心地听别人发言,讲话时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谦恭地声明,对这些被奉为地上的宗师和神的使徒的继承人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决不是审判官 ”(《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471页)。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