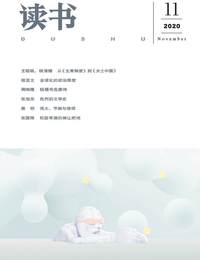“正直的老鹰”与“卑鄙的鸽子”
作者:读书
2020-11-27·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370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王升远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免职回国后,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做了一番深深刺痛日本人的评论:当然,德国的问题与日本的问题大相径庭。德国人是成熟的民族。
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 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四十五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四十五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十二岁的孩子。
正如任何处于受指导期的儿童,他们易于学习新的规范、新的观念。你能够在他们那儿灌输基本的概念。他们还来得及从头开始,足够灵活并接受新的观念。( 约翰·W . 道尔著、胡博译:《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版,540 页)
演讲中,麦克阿瑟毫不掩饰美国君临日本的家长式权威,他在炫示美国对日绝对统治力的同时,亦强调了欧美文化视野下日本巨大的“ 可塑性”。当然, 这种正面意义上的“ 可塑性” 又几乎与另一个令人忧虑的词—“不确定性”如影随形地纠缠在一起。在英文中,“ 不确定性”(u n c e r t a i n t y)一词意味着“令人无把握的局面”。而帝国日本的近代,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巨大“可塑性”的年轻国家,在“非计划性和非组织性”的近代化道路上横冲直撞、给亚洲地缘政治制造了巨大的“ 不确定性”, 又进而发展为“令人无把握的局面”,并最终灰飞烟灭的历史。正如丸山真男所指出:“ 正是这种非计划性才推动了‘共同谋划’的进行。这里存在着日本‘体制’最深刻的病理。”(《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二○一八年版,87—88 页)对明治以降的体制性病弊之反思是战后初期日本思想界的一项主要议题。却顾所来径,或为往昔思咎省己,或为来日杜渐除微,人们寄望于通过历史回望,探求天皇制国家盛极而崩的病理,重审被这段残酷历史无情操弄的自我。回望历史,识者惊觉当下日本的重大政治问题和思想困局,大多能在明治时期找到或隐或显的病源。
围绕这一议题,思想界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讨论集中在二○一八年,即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这一年,马国川出版了其“日本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中信出版社二○一八年版)。作者坦言:“作为一个记者,我愿意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愿意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较之于探索大国崛起秘密的《国家的启蒙》,马国川新著《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中信出版社二○二○年版,以下简称《国家的歧路》)则旨在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日本近代史为域外镜鉴,为新兴市场、后发国家的发展寻求有效的历史经验。以马国川讲述的帝国往事为起点,解析“非计划性”中的诸种因素以何种作用机制推动了“共同谋划”的动态形成,进而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揭示昭和初期日本政、军、商、学各界、各派之间聚散离合的力量关系,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日本近代化歧路背后之历史结构的理解。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