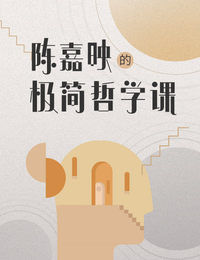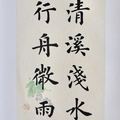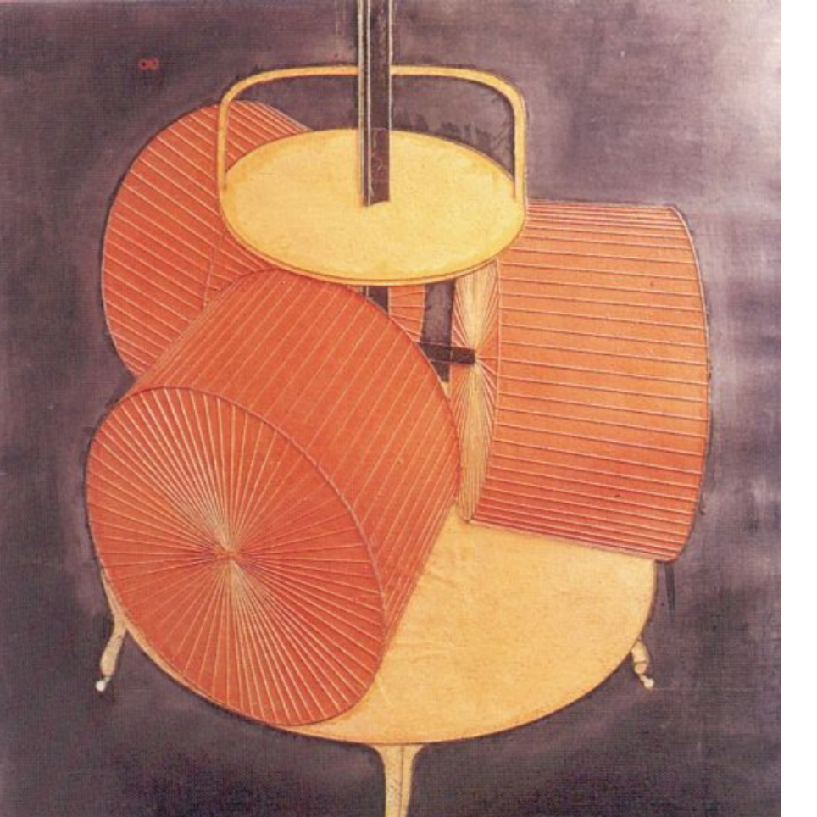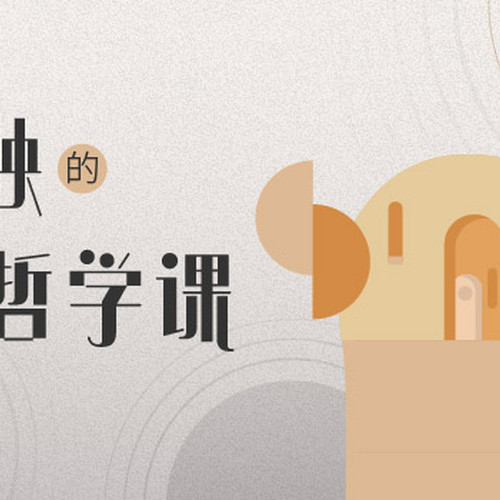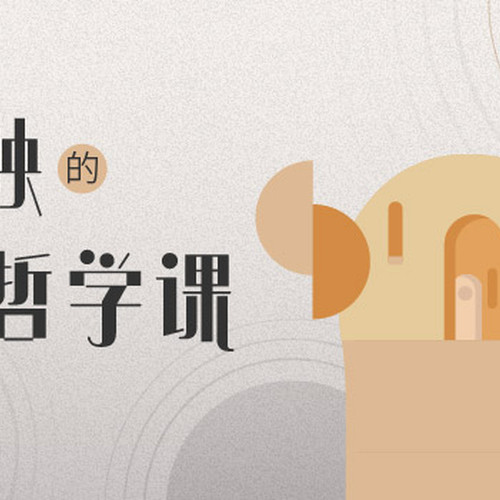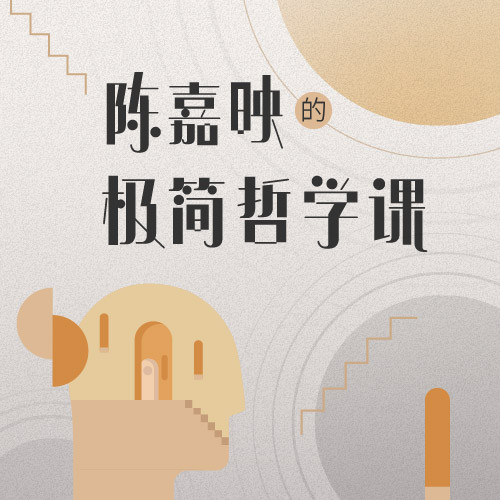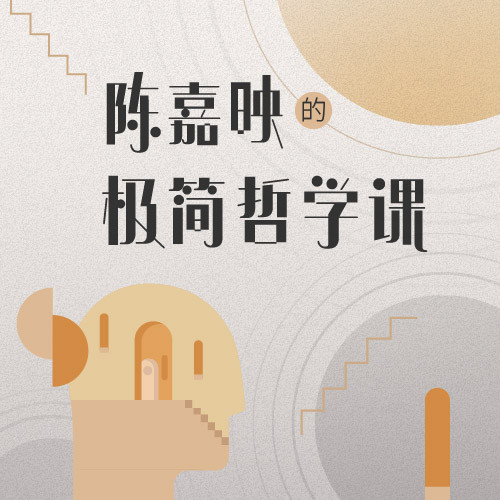1.3 能否用科学论证的方法进行日常说理?
作者:陈嘉映
2021-04-26·阅读时长5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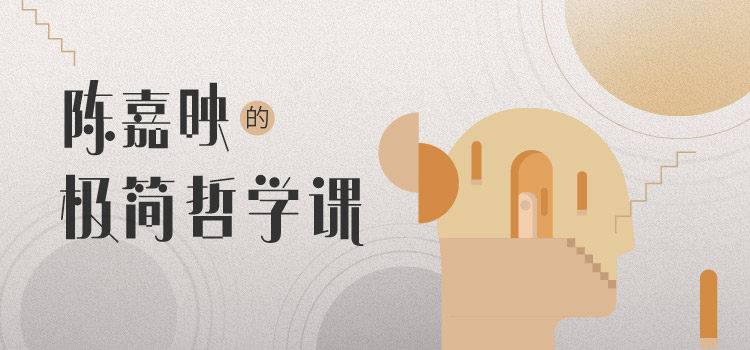
科学是怎么做到,把它的词汇明确化,把它的语境条件化或者明确化,或排除在外或考虑在内呢?
我们要是弄清楚了科学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能不能帮助我们在日常说理,在社会政治上的说理,也达到更加科学的这样一个水准,使它更有力更有效,使我们更加容易达到共识。
这当然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广大的领域,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整个展开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很简单地说一下,词象的含义变得明确起来。
日常说理是众多语境因素的集结
我们可能会想,只要我们清楚地加以界定,清楚地加以定义,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所使用的词汇变得明确起来了,但其实这是一个远远超出定义或不定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用科学词汇来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描述语和我们日常用的描述语区分开来。
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远近冷热”这是我们平常最会用到的一类词汇。比如说我到这里来,主人问我你家离得远吗?我说不算远,但也不算近,这里我们的对话是很清楚的。但是这里头却并没有告诉我们远和近是有多远、有多近,而且这远近,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估计是有关的,也和你是开车来、骑车来、走来都有关系。
讲冷热也是这样,我说今天天冷,也许跟我同行的朋友们说今天不冷,今天挺暖和的。
为什么远近冷热这些语词,在我刚才讲的意义上,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这个原因是由于,我们是连着自己的感知,连着自己的情况在谈论天气、谈论路程的。
比如冷热,是我感到冷热,那么有人可能会从这个角度说,冷热这两个概念,这一组概念是完全主观的,但是我想说不是这样的。冷和热肯定不是完全主观的,冬天冷夏天热我们都知道,我只说它其中,的确如果用这样的语汇说的话,的确含有主观的因素,不是纯客观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主观,但它也不是纯客观的,这样说就比较清楚。

我们在科学研究中,逐渐就要把这种带有主观因素的词汇,慢慢把它剔除掉,然后把它们换成纯粹客观描述的语汇。
比如说我们用公里数来代替远近,比如说我们用温度来代替冷热,这样的话就不管谁来感觉,谁来言说,大家就找到了共同言说的尺度。
然后我就说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说理,那不就语义明确了吗?你就来想一想,为什么你到一个主人家去做客的时候,他不问你,你家离这里是几公里?他问你们家远不远?
因为这是一个最便捷的,把环境跟你所要说的客观的里数结合在一起来问(的方法)。
所以有人会说,我们用数字来说话,好像这个是最准确、信息量最大的,我举过这样的例子,参加了一场考试,然后回到家朋友就问我了,说:“你考得怎么样?”我说:“这回考糟了。”然后他说:“你考糟到底是考了多少分呢?”我说:“我考了65分。”你认为是“考糟了”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还是“65分”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完全要看特定的情况。
也许65分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也许65分是个很糟的成绩,你告诉他65分,这些信息都没有说出来,而你告诉他考得很糟,你却把他要问的事情就给回答出来了。
这个“很糟”,显然集合了很多语境的因素,比如说你考的这门功课平均成绩是多少,你需要的成绩是多少?你自己的期待是多少,你自己的判断是怎样的?都集合在这样的一种言说中。
在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也包括我们平常说理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采用那种高度分析的方式来说,因为那种说往往反而不得要领。
比如说我们现在秋收也收完了,现在统计就出来了,我们今年中国的粮产量是多少吨,可以给你很好的数字,但是你听了之后,你不知道今年的产量到底是怎样。而你如果说,今年我们秋季的产量出乎意料,或我们今年的粮产量还是一个增长的态势,你就知道我们大致的农业情况。
有些概念无法剥离人类的感知去讨论
这是就两个极端而言,我一边讲科学,一边是在讲我们的日常言说、日常说理。而我们讲到科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还有一些科学,或者至少一些学科,他夹在这两者之间,比较突出的,就是社会科学。
我们经常会问,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它是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是科学,针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始终是有争论有讨论,也被研究着。当然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话题,跟我们这里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也不需要回答这么巨大的问题,我只是从刚才语义明确这一点,来谈一谈社会科学显然处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社会科学尽量不使用那种带有比如说情感色彩的,带有过分的时代色彩的这些语词,它会尽量使用那些比较中性的、似乎是可以良好定义的词汇。
但是,一方面,它不大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的那些词汇的明确性和稳定性;一方面,当它逐渐地使用这些中性语词的时候,也脱离了我们谈论社会和政治现象所用的那些语汇,乃至我们又觉得很陌生,就不太知道这些社会科学到底是在谈一些什么东西。
这里还有个更加深一层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是那些我们人类无论这样认识它,还是那样认识它,对它都没有改变的那些现象。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就比如说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多少?这个问题无论是希腊人回答,还是阿拉伯人回答,古代人回答还是现代人回答,或者说人们想到这问题,没想到这问题,人们答得出这个问题或者答不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变的,它的距离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但是有些问题就不是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幸福这个语词。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对所有的这些语词都希望给出一个中性的界定,然后把它指标化,我们就可以说幸福是如此如此的。但是,幸福就和距离不是同一类的概念,它一定跟那个谈论幸福的人有关系。就是说,提到幸福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不管你是怎么看待幸福的,是幸福就是幸福,是不幸福就是不幸福。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因为幸福是什么这件事情,和我们人类怎么认识幸福是连在一起的。
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去研究一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是中国的宋朝人过得幸福,还是欧洲的基督教徒过得幸福,我们去研究。那么我们拿出11个指标,一衡量,我们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或那个结论。
但是真正的研究,显然要加上一个因素,宋朝人是怎么看待幸福生活的?基督教徒又是怎么看待幸福生活的?如果这些基督教徒认为不信仰上帝就不可能获得幸福,给了他一堆指标,你说不管你怎么认识幸福的,你的确就生活得很不幸,他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他幸福不幸福,是跟他对幸福的认识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一开始讲到,说科学——我讲的是自然科学,它要达到词汇的明确性,细的不讲,我们最粗糙地讲,就要从词汇中清除掉跟我们的感知和认识有关的那些因素。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概念,等你把这个跟我们有关的感知和认知清除掉之后,这些概念不说变得没有意义,它至少变得高度的残缺不全了。
转发与分享下方海报
在观点纷繁的世界里,成为清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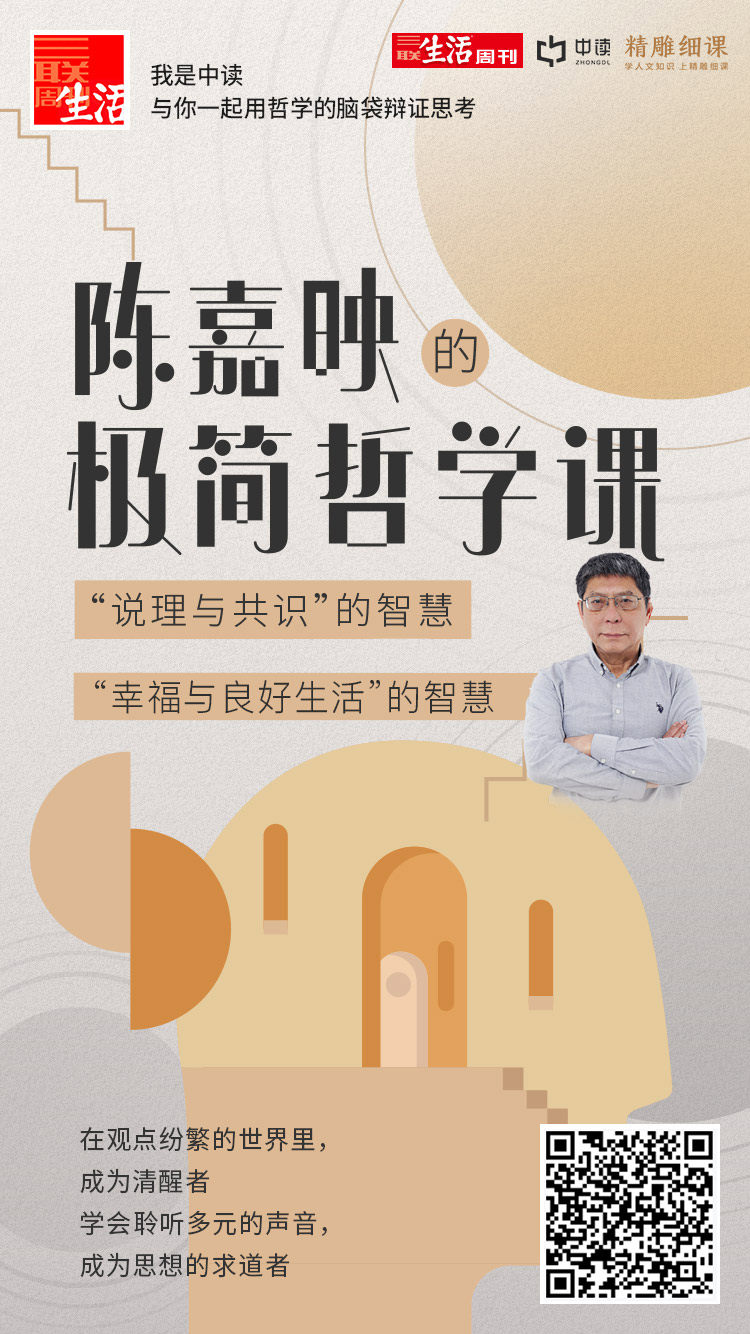
文章作者


陈嘉映
发表文章19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926人
当代著名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