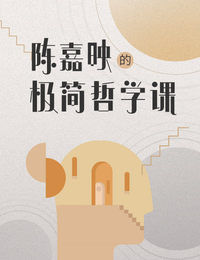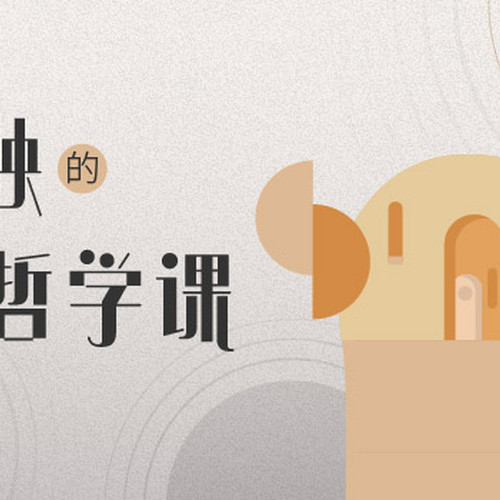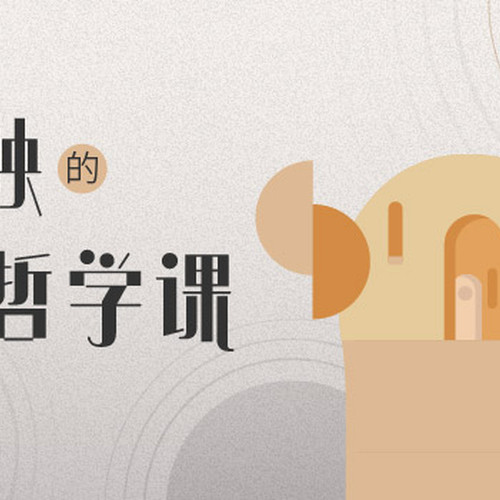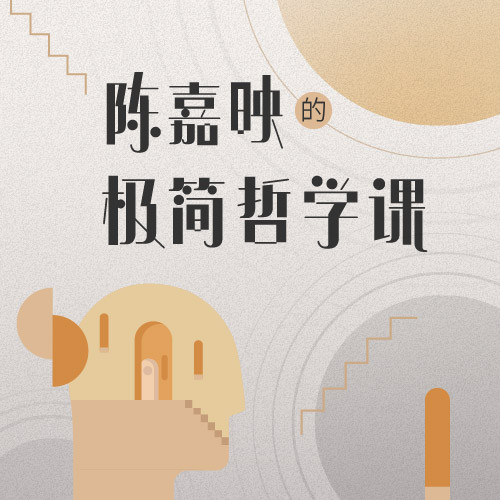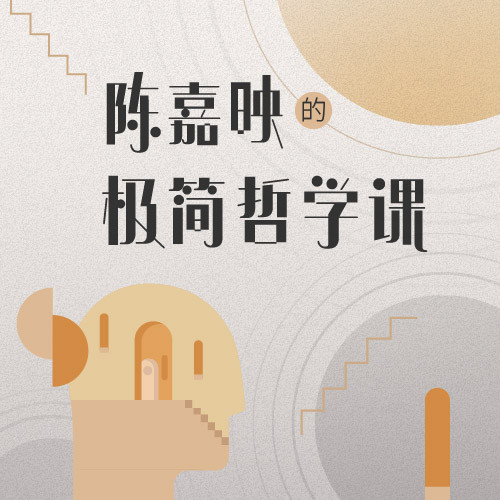1.4 概念考察:到底哪类东西叫共识?
作者:陈嘉映
2021-04-26·阅读时长5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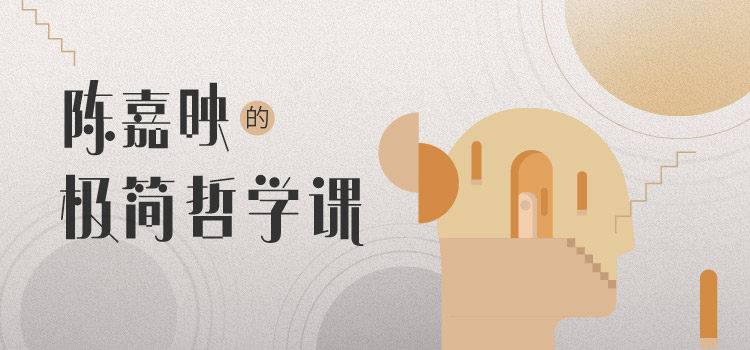
我们刚才讲的是科学和我们平常的说理,然后我们就讲到社会科学的一些说理论证,看到社会科学有点夹在我们平常说理和科学论证的中间。
我们今天当然特别需要社会科学,因为我们的世界现在变得那么广大,没有谁知道哪些是确定的事实,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些事实,关于这个,社会科学都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在达成共识这个方面,社会科学的帮助相当有限,这与我之前讲到的这些条件有关。
事实上也是。你看我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各门社会科学发展都很迅速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达成社会共识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哪怕是经济学这种相对来说科学化程度更高的领域,实际上关于经济的发展,也仍然不大能够提供很多共识。
那么,现在我们说到共识,渐渐地就露出了一些分歧。
两个角度来看共识
我们最早讲到共识的时候,是讲得比较笼统的,现在来看,这个共识大致至少可以分成两大类,或者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共识:一类的共识讲的是在事实方面的共识;另外一类是“我们应当怎样做”这个方面的共识。
我们会看到,科学有助于我们达到共识,实际上在自然科学中差不多到处都是共识,只有在很尖端的、很前沿的问题上会发生争论。而这些争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变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我们从小就学习这些科学,虽然我们要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对我们学到的科学知识,我们大致都是能够接受的。但是这一类的共识,并不能够自动地把我们带向我们应当怎样做这一类的共识。
我们所说的说理,其实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达到我们怎样做的共识。
但是我们发现前一部分,也就是关于事实的共识,是相对比较容易达到的,而要达到后一类的共识,就非常困难。别的不说,至少就讲到一点,即使你跟我都承认这一批同样的事实(也很难达到后一类的共识)。比如说美国人要选拜登还是选特朗普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争论。即使事实都摆在那里,各种不同的事实都应该有怎样的权重,单讲一个事实到底有多重要,这一点事实本身是不能够提供的。

这样自然就带来了问题,事实虽然摆在那里,但是一半人觉得,我们应该基于这些事实去选拜登,另外一半人觉得,我们应该基于这些事实去选特朗普。
至于说我们刚才讲到要达到共识,有好多不同的手段,比较温和的,通过宣传等等,比较恶劣的,通过胁迫等等。我们在上下文中讲到的共识,其实都讲的是达到“怎样做”的共识。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不是说这些因素都完全不起作用,但是它们的确不是内在于科学说理的因素。
因此,从比较长的时段来看,科学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事实方面的共识,但是它仍然不能够达到怎样做的共识。而在怎样做的共识这方面,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因素,比如说宣传,甚至威胁、利诱、胁迫这些因素,就会起到大得多的作用。
共识不止于达成结论
而且共识这个概念本身,也值得探讨一下,也就是说,到底哪些东西我们叫做共识,这个事情本身也值得考量。
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谈判。谈判也被看作是通过说理达到共识的一个重要的人类活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在进入谈判之后,在说理之外的很多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比如中国在1840年之后,和外国签订了很多条约,这些条约没有一样不是通过谈判达成的。比如说我们最后签署了《辛丑条约》,我们赔了4万万两白银等等。一大堆的条约条款,都是双方同意签字的,而且都是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经过各种讲理来达到的,但是显然条约不只是一个说理的成果,在谈判背后强权等等这些因素都起着作用,而且可能是起着更根本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讲到共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在讲,我们对于怎样做取得了共识,但是即使我们关于怎样做取得的共识,就像我刚才用《辛丑条约》做例子来说明的,但是这个到底叫不叫共识,本身又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是在结论上达到共识,在怎么做的结论上达到共识,这如果叫做共识,也是一种非常边缘意义上的共识。
那么我们在讲到共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是说,这个共识基本上是基于说理达成的,也就是道理和结论之间有一个紧密的联系,而不是说这个道理跟结论之间只有一个微弱的联系,这个结论更多是由其他的因素造就的。
实际上共识这个词,在报纸上、在媒介上我们更常常听到看到,恰恰是在谈论谈判,比如我们说两方的谈判达成了共识。
这里面我想顺便说一句,只是来解释一下我对于共识的理解。就是这是一种政治话语,本来这些谈判背后,远远不只是一个共识的问题,而是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手段,政治手段背后又有暴力、强力等等这些。但是把它说成是双方达成了共识,或者多方达成了共识,这就是一个eulogy了,就是一个好听的话,所以共识这个词,本身有时候就要求我们做进一步的反思。

说理活动通常是借助于、或纠缠于其他因素达到效果的
现在我们转到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开始讲到,我们希望只要是严肃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那么我们总能够达到共识,因为我们都是一些理性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我们已经讲到了,即使一批事实是双方公认的,他们要达到怎样去做的共识,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实际上最大的距离是在这儿,而不在于确定那些事实。
至于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就更加可疑了。因为如果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可能一开始就不需要谈判,也不需要你去说服对方了。如果你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指的是更深一层的道理,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你我的道理讲不通,但是我们通过更深地挖掘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在道理的最深处道通为一。
道通为一这个话,也会牵扯出好多复杂的考虑,我在这里只说一点,就是纯粹的道在深处融会贯通,即使你这么认为,那么它对解答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分歧,它的帮助也不大。因为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几次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矛盾,这些冲突、这些分歧,道理在其中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有些它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有些它是利益冲突跟其他的冲突结合在一起的冲突。那么在政治社会领域中,你要改变他人的看法,仅仅靠讲道理,几乎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也并不是否认讲道理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种活动,而且我们也的确有时候通过讲道理获得共识,或者至少在其他的因素都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能通过讲道理获得共识。
我们刚才也讲,回忆我们自己说理的情况,经常会有那些沮丧的例子是吧?说了半天道理也没有说通,但是反过来,我们显然也能找到另外一些积极的例子,就是的确通过说理就说服了一个朋友,或者像我们夫妻之间,也可能丈夫说服了妻子或者妻子说服了丈夫,是通过说理来做到的。
那么我想说的,并不是要贬低说理的作用,而是不要把说理活动看做一个太单纯的活动,无论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中,说理都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它达到的效果通常是借助于其他的因素,或者纠缠着其他的因素,达到它的效果的。
转发与分享下方海报
在观点纷繁的世界里,成为清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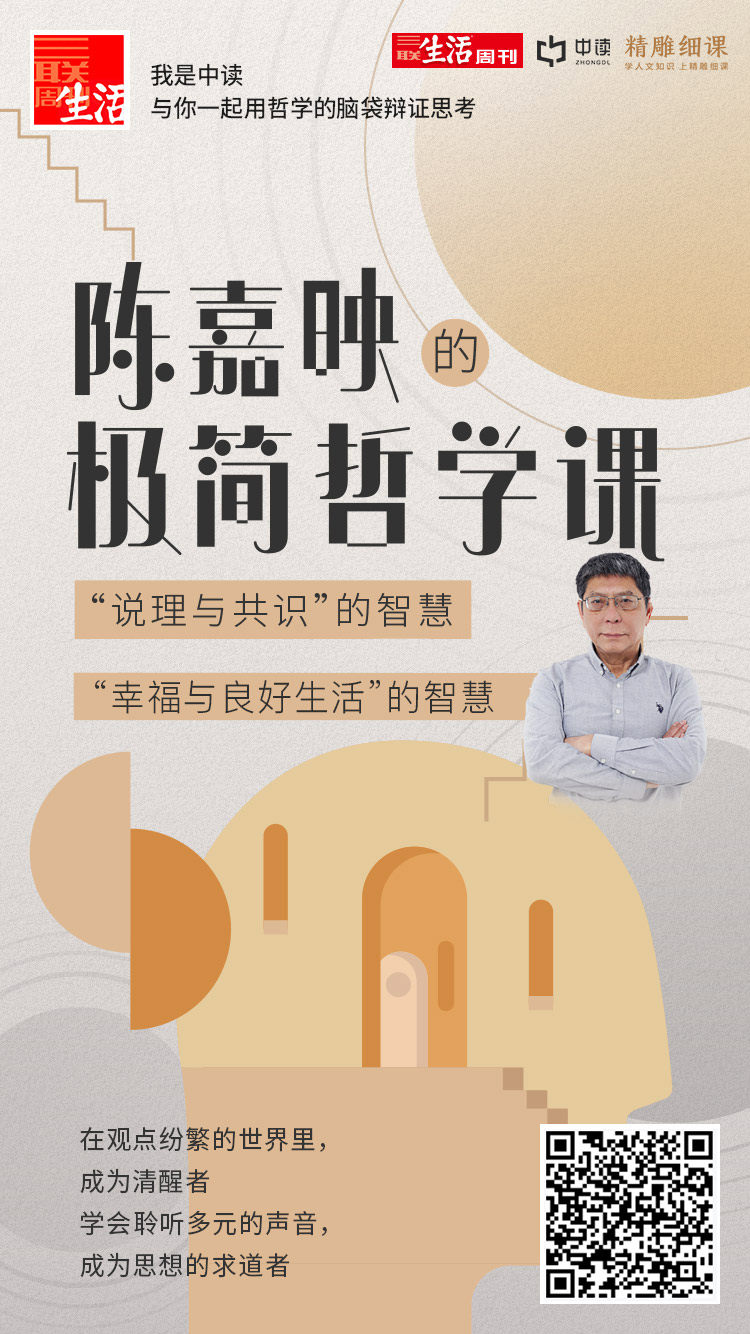
文章作者


陈嘉映
发表文章19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926人
当代著名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