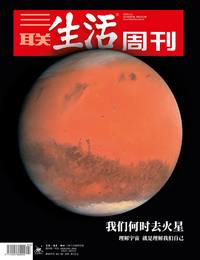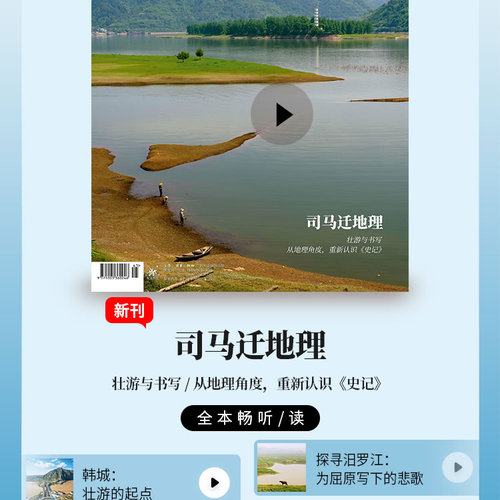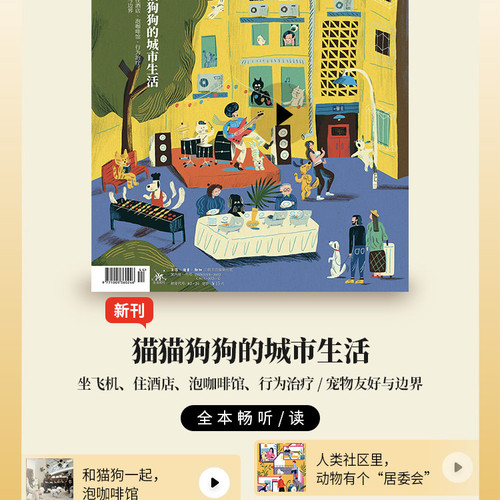苏笑柏:出漆,入画
作者:曾焱
2019-01-16·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715个字,产生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漆与画
苏笑柏将他现在上海的工作室描述得像个巨大的热气腾腾的车间,“但是”,他强调,“里面有最好的墙面,最好的地面,最好的灯光”。做漆是精妙的功夫,好坏毫厘之间,来不得半点偷工,必须每一步都做到位。
布面油画开始创作之前,画家要在框上先绷画布。在苏笑柏这里,他先要做的是“胎底”,这比绷画布复杂太多,需匠心,也需体力和耐性,还有一点点运气。
胎底他百分之百按照传统工序来做,每次费时至少3个月。先选用东北杉木板拼接最轻的一种挤塑板做底,挤压成型后,用锯子将表面和边缘处理成他理想中的弧度,“就像女孩的肩膀”,他描述那种微妙的视觉的“触感”。
为什么画板要做曲面而非平面?他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并不完全相同的解释。比较令人遐想的一个讲述,来自他2003年在福建的6个月,他说那时候收集了不少古瓦片,古代工匠的细节处理让他常有感叹,比如,每一个瓦片的形状会有微妙的起伏,而这便是他后来将画板做成曲面的灵感来源。
在古代,所谓漆器,漆附着于器,其体面往往是有弧度或凸凹的,不同光照下,漆色乃至质感就会产生许多微妙的、无法预料的变化。王世襄形容他所收藏漆器中的一件清代木胎葵瓣式捧盒,就曾说,“有闪光而隐约不宣当是所期之效果”。
接下的“裹衣”,是在胎底上面用漆贴一层亚麻布,等它干得坚实以后涂上漆泥,也叫上腻子;再裹衣,再上腻子……如是三道功夫才算完成。这种工艺是从传统漆器的花瓶而来,只不过花瓶里面用的是泥胎,等外面器形干透以后,再把器物放到水里去泡,最里面的泥胎最终会被水化掉,这就是“脱胎”。苏笑柏说他也曾试验过,想仿照脱胎的原理将画作里面的胎底去掉,但没有成功。所以他每件画作在全部完成之后,往往有四五十公斤之重。

“我对漆的继承就到胎底为止,从胎底之后的所有创作,都是对漆的反叛。”苏笑柏不止一次校正我对他绘画的观感。
“开始是大量看书,记很多笔记,完全按照古法来,但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方法,比如调色,我的审美趣味就和民间师傅们有极大差异。”
漆无法调出洁白色鲜的颜色,所以传世实例也极少单纯用漆色作画,而大都是漆色和油色并用。苏笑柏的试验是在大漆里加入西方油画的颜料、滑石粉、调色油,调制特殊的颜色和质地。他有意褪掉漆的光泽度和细腻度,在各种温度和湿度之下摸索漆的脾性,琢磨如何让局部氧化、龟裂……他用的很多方法其实是对传统工艺的反动。
古代漆器传世绝少,现在我们所见的,大多出自墓葬。苏笑柏生长在武汉,这座城市的湖北省博物馆就收藏了国内最好的楚地出土的秦汉漆器。但在学校的时候,他和同学们眼里只有从西方传过来的现代主义,对这些文物完全不感兴趣。“现在我却变得着魔,每年至少飞武汉看一趟湖北省博物馆。在国外也一样。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我进卢浮宫就找德拉克洛瓦,看安格尔。现在是每次都直扑埃及馆,看两河流域,看那些人类文明留下的痕迹。”苏笑柏说,就是站在那些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绘画面前,斑驳的画框对他的吸引力也大过油画本身。“年纪大了,看博物馆的兴趣真是完全不同从前了。”
文章作者


曾焱
发表文章58篇 获得8个推荐 粉丝2114人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