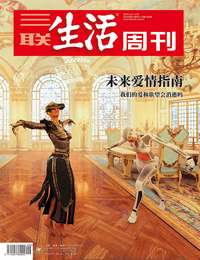拯救抑郁少年:陪伴与疗愈
作者:黄子懿
2019-01-28·阅读时长1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8875个字,产生6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青春暂停键
48岁的李玥一度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女人。
她来自重庆县城,勤快能干,在当地社区工作,兼开一个茶楼,年收入可观。老公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当老师,工资上交,家事由她。儿子杨玉明成绩优异,中考前即被重庆某国家重点中学录取,全校只有三个名额。
“我那时真觉得他一只脚都踏进好大学了。”那时的李玥干劲满满,早出晚归打理生意,为儿子铺路。每次考试,儿子都会带来好消息。但某天,儿子从市区打来电话:“妈妈,我肚子疼。”
2014年上高一后,儿子始感腹部胀痛,睡眠不好。李玥带他检查,确诊为中度焦虑,后发展为重度抑郁。当初儿子来电时,她还觉得这是“瞎折腾”,从未想过那个电话成了她生活的转折点。如今,儿子因抑郁症已休学两年。
在这个青少年抑郁症疗愈的亲子营现场,很难不注意到李玥。她身材不高,憔悴的面容中略带笑意,在现场来回奔走,负责登记家庭信息,安排一对一咨询。不时会听见她吆喝着:“××号家庭,到你们了。”亲子营负责人张进说,她很能干。
张进曾是媒体人,2011年罹患抑郁症后,生活重心发生转向。在一年治疗康复后,他写了抑郁症诊治的书《渡过》,并开办公众号进行科普。几年来,聚集了一批读者和患者的“渡过”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抑郁症社群。
一位社群元老说,因为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社群里的家长人数这两年增长“几乎是爆发式的”。“渡过”社群包含读书、写作、跑步等一共29个微信线上群,家属板块共9个,全是家长群,人数逼近5000人。咨询时,焦头烂额的家长们往往还没开口,就几近哽咽。
“渡过”会定期聚集康复者、医生和咨询师,举办线上家长学堂。但张进逐渐发现,很多实际问题需要面对面解决,尤其是当亲子关系需修复、社交恐惧待克服时,青少年抗抑郁背后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太多家庭和孩子需要拯救,那是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觉。”一位家长说。
2018年12月30日,“渡过”第二期亲子营在苏州开营。当日苏州下大雪,雪花落身,寒冷浸体,像是在呼应这些家庭的心境。张进说,本打算招22个家庭,但报名者太多,最后扩大至36个家庭,其中有8个家庭参加过第一期杭州营。
李玥在营里既是参与者,又是志愿者。她与张进相识于2017年4月,儿子抑郁最重时。那时张进计划写新书,拟寻访中国有代表性的抑郁症病例,有读者就建议他关注青少年群体,称后者已成发病高峰。张进当时觉得还没能力碰,“这是最复杂、最难的一块。因为青少年患者正处于人生关键期,很多东西都叠加在一起了”。但事与愿违,张进采访时不断遇到青少年病例。当他还在第一站贵州时,就有几位川渝家长找来,李玥是之一,她主动驾车到贵州接张进。

“做亲子营并不要什么灵感,找来的家长实在太多了。”最后成书中,张进记录了13个病例,超过一半发病期都在青少年。张进说,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研究显示,中国10?24岁青少年、青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自2005~2015年间显著增加,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高于男,且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那次见面,张进看到李玥的儿子杨玉明,立刻明白他正受煎熬。男孩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曾翻过天台,也拿过菜刀,狠狠划手腕,血流成河。家人需24小时看守,防他自我了断。在开营式上,杨玉明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36组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患者仅9岁半,最大的29岁。营内处处有“雷区”,哪怕是在室内课堂,都时有争吵、哭泣,或是少年们摔门而去。一天,一行人参观苏州丝绸厂,一位女孩突然对妈妈吼叫,厂里养的蚕勾起她的不好回忆:她童年养的蚕都被妈妈扔了;另一位妈妈则在报到时眼泪汪汪地说,来时的车上,女儿将一杯水泼在她脸上。
张进说,抑郁症和压力有关。压力下大脑产生应激反应,身体高度警觉,调动生命潜能应对危机。危机缓解后,大脑会关闭反应,休养生息。一旦压力持续,应激反应长启不关,慢性压力就会让身体机能耗损,引发抑郁。抑郁症也有易感群体:敏感、自省、自我要求高、完美主义等。
“得抑郁症的孩子,往往都是好孩子。”一位父亲感慨。来到这里的孩子,多来自重点中学,原本成绩优异。营内带病帮忙的志愿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学生。然而,这些美好的人生旅途,都被按下暂停键。
文章作者


黄子懿
发表文章75篇 获得47个推荐 粉丝700人
不得拉稀摆带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