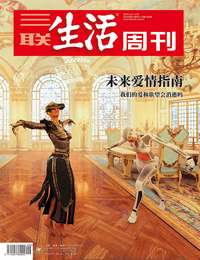韩东:为人类的敏感性写作
作者:艾江涛
2019-02-11·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373个字,产生1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温柔的部分
一年多前,韩东把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江边的金鹰当代艺术空间。这里环境清幽,树木林立,即使大白天也没有都市的喧嚣之声。如果没有特别的事,韩东每天上午到工作室,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再回住处。1993年辞去南京财贸学院政治教研室的公职,成为职业作家后,这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不同的是,那时他的工作室位于秦淮区的瑞金路,从1984年他调回南京工作起,那里便成为南来北往的诗人朋友的据点。韩东在文章中写道:“我的住房条件稍好,在瑞金路有一处空房子,被我当作工作室,且门锁形同虚设,用一张硬纸片一别就开。经常有外地的诗人找我不遇,当地的诗人知道这个诀窍,就领着他们自己开门进去。”
工作室里除了几架书,就是座椅和用于写作的台式机。在湿冷的南方,韩东将自己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一次次打开频繁跳闸的空调。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苦修的隐士,而非人们想象中那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叱咤风云的诗坛大将。
作为“朦胧诗”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韩东最初以带有解构意味的口语诗、随口谈及的“诗到语言为止”知名。1985年创办的民刊《他们》,更使他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中心人物。随着世纪末诗坛的分裂,韩东与于坚、伊沙等人成为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的“民间写作”阵营的代表。进入90年代,韩东将大量精力投入小说乃至电影剧本、舞台剧的创作。不过,不同于许多转行的同道,他始终没有停止诗歌写作。另一方面,随着1998年与作家朱文联合发起堪称行为艺术的“断裂”问卷调查,主动选择与主流文坛隔绝,加入各种诗歌论坛的论战,韩东似乎越来越成为文坛的异类。
见到韩东之前,我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在各种争论与事件中所见的那个激烈决断的韩东,似乎与他那些带有敏锐感触的温柔而忧伤的诗格格不入。这种感受在我读到他创作于1985年的那首代表作《温柔的部分》时变得尤其强烈。诗中,韩东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我甚至揣想,诗歌对于韩东来说,是否就是取舍之后那温柔的部分?
我们的聊天,很自然地从那些寂寞的乡村生活开始。1969年,8岁的韩东随父母一起从南京被下放到苏北洪泽县的乡村。在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前,韩东在那里一直生活了9年时间。某种意义上,那里才是他抽象意义上的家乡。他告诉我,他常常梦到回到当年下放的地方。父亲领着他和哥哥在自留地里种菜栽树。上中学后,他要和同学一起下地完成捡粪的任务。那是一段与大自然,还有人的本真状态更为接近的时光,也让他获得了一些书本之外的知识。“很多人不知道母鸡离开公鸡,无法孵出小鸡。因为母鸡会下两种蛋,没有受精下的蛋是孵不出小鸡的。”带着一丝小小的得意,韩东将话题迅速转移到对知识分子的反感上。“我讨厌知识分子的自我感动和优越感。写诗的人当中,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读过书有知识,其实只要是个聪明人,大脑没闲着,从生活中照样能获得知识,只是和你的知识不一样而已。”
文章作者


艾江涛
发表文章131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679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