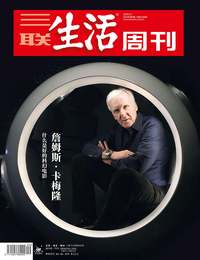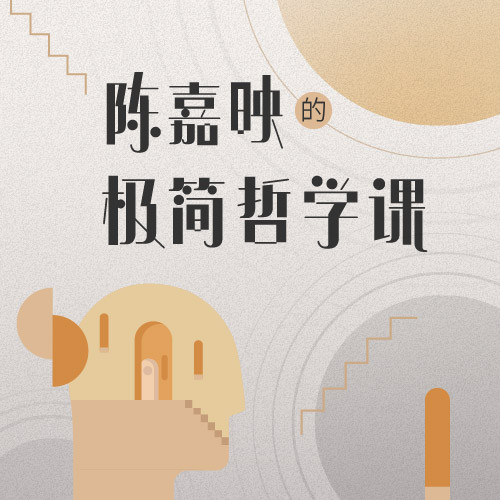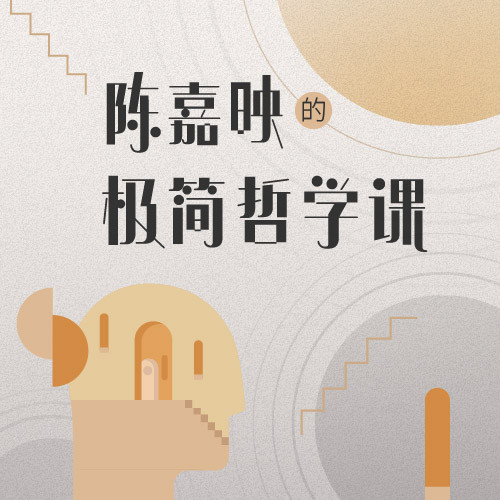香港油麻地导赏团:繁华背后的阴影
作者:黄子懿
2019-02-28·阅读时长1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8311个字,产生4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摄影/刘有志
“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
油麻地坐落在九龙南部,和香港的两大人气聚点尖沙咀和旺角毗邻,三区统称“油尖旺”。但与其他两区的光鲜亮丽不同,油麻地是相对黯淡的,像是夹在二者中间的洼地。
油麻地的招牌是庙街,上世纪90年代黑帮港片的取景圣地,时至今日夜里依然摊贩聚集,灯火通明。庙街中段一街之隔,有一处白色多用途的政府大楼,下层有垃圾站和厕所,上面是社区图书馆和多层停车场。停车场入口处,一座天桥从西直穿而入,又从东穿出,像是一把利刃刺穿一个躯体。
“这是因为先有这栋大楼,再有这座天桥。”住在油麻地的33岁律师陈玉峰对一群人说,“眼前这栋楼,可能是油麻地死过人最多的地方。”她以大厦西侧一层的一栋公共厕所为例解说,那个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男厕基本每个格子都死过人”。
这还不是全部。这座大厦的停车场高8层,每层都有窗户向四面开放,可从各个方位跳下。过去几年里,每年都有人在不同方向、楼层一跃而下。2016年中秋前夕,一名男子从8楼跳下,砸到一名中年女保安,导致后者重伤,男子亦身亡。据当时香港媒体报道,事发后,现场一排大排档唱歌摊无惧命案,生意照做。有人载歌载舞,高唱:“命里有时终须有。”


“我曾在这块政府用地住过5个月,但从来不知这里死过这么多人。”一个20多岁的参与者说,若不是2月16日夜里的导赏团,他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些故事和细节。他所参加的导赏团叫“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由陈玉峰和陈可乐策划并带队,这座政府多用途大楼是第一站。
导赏团是香港的一种特有公众服务形式,意思是策划并带领一批市民去了解某个特定专题。重口味的“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导赏团于2016年下半年创办,在秋冬季周末举行。两小时内,陈玉峰和陈可乐会带着参与者走过1.5公里路线,参观并讲解油麻地约10个死亡现场。“两万种死法”一名源自美国冷硬侦探小说《八百万种死法》,“八百万”特指纽约的800万市民,每人都有各自的死法。无人可逃,尤其是在纽约这座大城市。
陈可乐今年30岁上下,热爱哲学,一直从事社会公共工作,对死亡和权力结构有思考。他说,这个导赏团的灵感来自于2016年万圣节,为呼应万圣节特定的“死亡”主题,他开始关注凶案,发现自己居住的油麻地就常有命案发生。陈可乐说,他希望通过做这个导赏团唤起人们思考,“为什么处在同一空间内,他们死了,而我们却活着?”
原本想只做两期,但报名者络绎不绝,于是从2016年10月第一期开始,一直做到现在。3年下来,他们带团超过50次,逾500人。“每一步发展都超出了预期。”陈可乐说,2019年初经媒体曝光后,档期报名人数一下猛增至300人,团队应接不暇。
两个策展人,陈可乐在油麻地住了8年,陈玉峰住了5年。他们觉得,油麻地几乎是最具香港气息的社区。它楼宇旧且不高,房租便宜,因而人口密集,各类人聚集穿梭,有少数族裔、等待难民身份者、露宿者等。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王惠玲曾在油麻地做过“香港记忆计划”的社区口述,她说,油麻地的最大特色是街道,只差一两条街,生活面貌已大不相同。“一些街道老老实实,晚上乌灯黑火;靠近弥敦道者,则一直灯火通明,充满藏污纳垢的夜生活。”很多港人也避之不及,每次有朋友来港在附近住,都会劝他们尽量靠近弥敦道,“越往里越黑,感觉越不安全”。
这与陈玉峰的观察相符。她平日在中环上班,爱好爬楼,常在油麻地各个高楼的天台穿梭,发现除弥敦道、庙街等地灯火璀璨外,这个社区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一片幽暗。而身为律师的她知道,那些幽暗角落一向有人生活与死亡,只不过很多人不敢独自去看。
陈玉峰与陈可乐选择了10件凶案讲述,多数发生在2012到2016年。陈可乐说,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标准,就是希望他们代表不同的群体。然而,这些案件也呈现出某些共性:死者几乎都是在此生活的边缘人,有打工的女孩、坐台的公关、南亚的移民等,多为女性。陈可乐感慨:“城市是会吃人的,香港繁华的背后也有很多阴影。”
文章作者


黄子懿
发表文章75篇 获得17个推荐 粉丝497人
不得拉稀摆带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