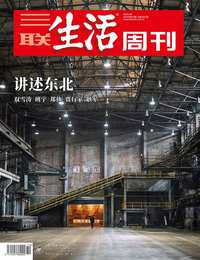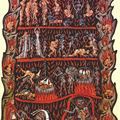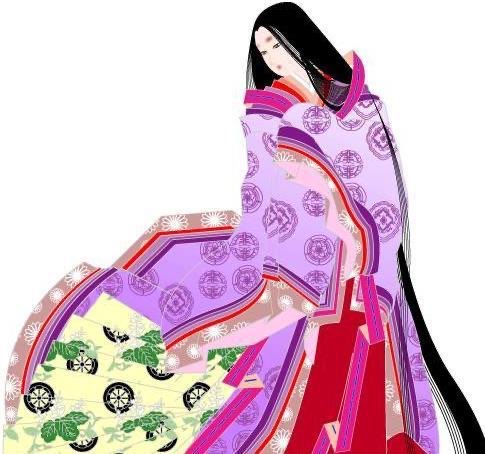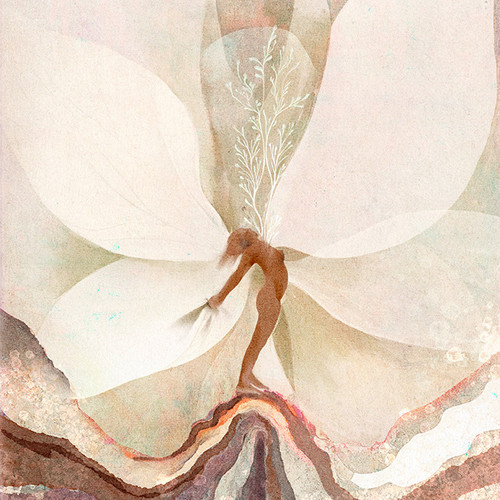专访梁鸿:东北是可以虚拟的
作者:孙若茜
2019-04-03·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268个字,产生7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作家梁鸿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梁鸿对新一代的东北年轻作家早有关注,双雪涛就曾是她所任教的人大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学员。从他们的写作样貌到集体“爆发”背后的社会动因,她都有所思考。
作为一个写作者,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再到《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等等,梁鸿也始终在书写自己的故乡。在她从非虚构到虚构写作的探索中,“梁庄”作为一个符号,几乎融合了所有的村庄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关地域性写作的话题及现实与文学创造的关系,也是她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
东北作家正在“爆发”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年,从双雪涛、贾行家再到班宇、郑执等等,诸多东北年轻作家的作品相继获得不同层面的认可,关注度高且广。从你的角度来看,“年轻东北作家群正在崛起”这种说法准确吗?
梁鸿: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少会说“东北作家群”。归结为“东北作家群”,好像是有点儿落后的一种做法。因为每个作家的个性可能都不太一样,现在很少会使用这样的一个群体性的命名来叙说一群创作者。当说到“群”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作家作为个性的一种存在,很容易被归结为同一种特性,虽然他们可能是拥有某种共同特性的,但我觉得这样做对作家本人的创作来说还是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所以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我并不觉得是一个“东北作家群”正在崛起,可能应该说是东北作家正在有一个爆发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他们会在近两年“爆发”?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梁鸿:我觉得可能这与整个东北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状况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东北是一个大的重工业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工业改革以后,工人下岗对工业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工人下岗,使得原来那样一种集中的、有福利的,那样一个我们曾经说是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忽然间变成了下岗的、无所依靠的普通人,没有生活保障。几万下岗工人的背后就有几万个家庭,家庭中有老人,有孩子,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性和不同的社会表达。
我觉得可能刚好到了现在,一二十年过去之后,东北这样一种工业的状况,大量的破产、下岗所带来的后果,慢慢沉淀到了实际生活里边,败落、疼痛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又是这一代年轻作家所体会到的,他们就是后果的承受者。他们还不像他们的上一辈,曾经享受过国家福利待遇,而是完全在一个破碎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大的社会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如你所说,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涉及到90年代东北的工业变革,以及在此变革之下的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你能以此谈谈90年代的社会氛围对于人和文学的影响吗?
梁鸿:90年代的文化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社会的变革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社会状态,新的人性的发展。整个商业社会对文化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90年代以后,我们都说文学被边缘化了,而所谓的边缘化实际上就是指传统的这种精神观念已经被新兴的商业观念所代替。
传统的精神观念,因为不能产生商业效果,自然地会对文学的地位、文学的生产以及文学的创作发生一个本质的影响。文学一定是跟社会和现实发生关系的,不管这个作家写作的题材和意义背后的承载有多么深远,它的故事肯定是与他的生活相关的。所以我觉得90年代东北变革所产生的新的形态,一定会成为新一代作家写作的一个基本主题。并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是一个非常大的书写范围,不见得一定要写问题,写人生就非常好。
文章作者


孙若茜
发表文章103篇 获得13个推荐 粉丝705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