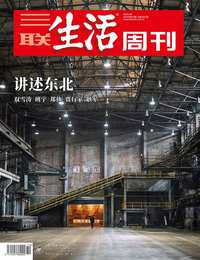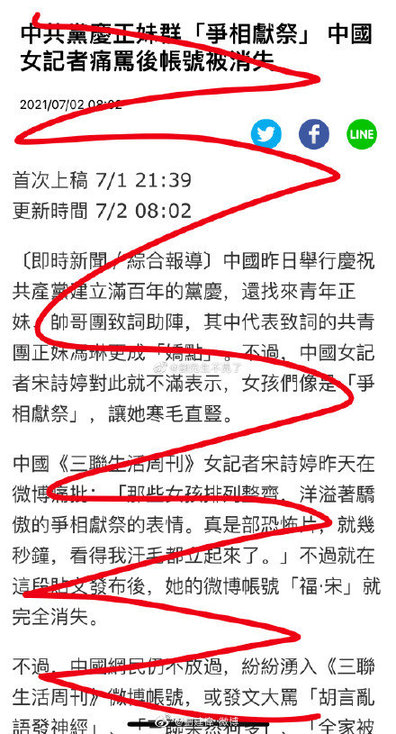后工人村时代
作者:宋诗婷
2019-04-03·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784个字,产生3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傍晚,在工人村散步的居民
口述/班宇 采访/宋诗婷
摄影/蔡小川
工人村那179栋三层红砖房早就不见了,只剩32栋,成了省级文物。其中7栋恰好围成大半个圈,组成工人村生活馆,算是对过去半个多世纪集体生活的纪念。生活馆对外开放,涂了层新漆,换了铝合金窗户,和另外25栋形成现代与前现代的对比。
出了半包围的院子往北走,南十马路上那栋小楼底层是个宾馆——纯莉博宾馆。“标准间50元至70元,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字幕不停滚动。晚上,宾馆招牌发出橘黄色的光,白色的LED灯郑重其事地打在上面,将这家小店照成工人村最亮的一角。
“每次路过,我都以为是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呢。”班宇一边走一边回头望。
高中以前,班宇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这片区域。那些年里,他和父母所住的变压器厂宿舍和工人村隔一条马路,距离不过几百米。《冬泳》里那个露天的文化宫游泳池在卫工街九路,也不过两三个街区的距离。某段时间,他和一些儿时的朋友经常去玩,除了他,别人都早已退学,也懒得上班,每天无所事事。那个把他带进摇滚世界的花鸟鱼虫市场在家与学校之间,从一个重点中学的学生到坠入愤怒与重金属世界的叛逆少年,只需五六分钟车程,自行车。
也就是从那时起,班宇的世界分裂成两个。一个是90年代末、2000年初中国东北冰冷的景象,父母下岗,城市凋敝,目之所及一片萧条。另一个是涅槃、枪炮与玫瑰,沈阳地下摇滚乐队疯狂与愤怒的演出现场。现实世界郁结的病灶流向昏暗的酒吧和俱乐部,在那里被展示,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被捅上一刀又一刀。
这两个世界恰恰促成了班宇今天的文学创作,冰冷的现实为小说提供书写素材,音乐和文学最终交汇,内化为他编织素材的方法论。
相较于那7栋楼组成的生活馆,班宇小说中的世界更具体可感,倒是真有点纯真博物馆的意思。只是那里不光有一个男人的爱,还有他隐藏在角落里的秘密和无法直言的控诉。
要在眼前这个工人村街区里寻找小说中的世界和班宇过去的生活是困难的,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景象来追忆,反而更加空洞,连语言本身都是尴尬的。
于是,班宇和我们都放弃了。走进一家最家常的馆子,锅包肉、红烧带鱼、凉拌拉皮、尖椒炒猪肝……还有八九瓶雪花啤酒和一个小瓶老龙口。一共151块,这是一个写小说的文艺青年这么多年留在东北生活的底气。
喝上酒,班宇说起话就更像他小说里的人了,语速快,句子短,感情色彩强烈,在依然挺冷的东北和破败的小饭馆里听,“贼他妈苍凉”。
以下为班宇的口述。

工人村滑梯上的孩子
关于“下岗”
关于“下岗”,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在铁西一个补课班补课,大概是1996、1997年左右,在重工街的一个幼儿园里,负责的老师叫衡长义,他本身不会讲课,但组织能力特别强,找了些很好的老师来帮他带学生。
有两个老师很特别,一个姓范,身体还有点残疾。蹬自行车时一只脚踩一下,脚蹬子空转个半圈,再踩一下。还有一个姓刘,以前在工厂上班。工人,外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文化,性格极其暴躁,经常打骂学生。我初中同桌的爸爸跟刘老师是一个厂的,说在这厂里,他基本是任人欺负的角色,很老实,没脾气。但这人身上有一股喜欢琢磨的劲儿,爱研究数学,还讲得特别明白。
那个补课班办得非常成功,别说铁西,在全沈阳都是有名的。有一阵子,沈阳号称要搞素质教育,到处抓补课的,很多补课班和老师都被举报揭发了。我那个班因为办得太大、太成功,很快就被干掉了。这个事情没问题,整个大形势就是这样。但我不理解的是,后来《沈阳日报》发了一个稿子,标题里赫然七个大字——“下岗职工衡长义”,内容就写他下岗,弄个补课班,着急招学生之类的,非常大字报。
当时我就受不了了,那会儿我父母还没下岗,正濒临下岗,怎么“下岗”突然就变成犯人一样了?我爸爸即将从一个工人变成一个“犯人”,为什么会这样?
1996年,下岗潮席卷我家。我是双职工家庭,爸妈都是变压器厂的。爷爷奶奶有三个孩子,这在当时不算多,两个姑姑也都有孩子。有年春节,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爷爷奶奶、我家、小姑姑家,还有其他亲戚,加一起十几口人,吃着吃着大家突然发现——全家还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就只有我爸和我了。
我一想,可不是吗?爷爷奶奶退休了,奶奶的妹妹在一个国营的浴池工作,浴池黄了,她就没了工作。妹夫还没到退休年龄,但也丢了工作。只有我爸还在上班,而我还在上学,更小的弟弟还没开始上学,家里的其他人又都下岗了,就我和我爸两个人有正事儿干。
算起来,我爷爷是离休,和退休相比还能多享受一点福利,其中有一项,是免费为离休者定期赠阅一份名为《晚晴报》的报纸,官方说法是为了充实离休老干部的业余生活。这份报纸的名字起得实在是好,“晚晴”二字的组合让人充满希冀,但这风景并不是谁都能看见的。
这算艰难吧?挺可怕的吧?生活会出现巨大的问题吧?但那些年过得也还挺好。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变压器厂宿舍楼里的大部分人也都下岗了,但好像每家都有自己的办法活下去,做点小买卖,去别的地方打工,有技术的搞点技术,没技术的出点苦力,都能维持个生活。
遇到事互相帮衬就必不可少了。比方说亲戚的孩子,或者我考初中,当时要缴纳一笔择校费,数额不小,基本上都是东拼西凑,今年我家借给你一些,明年还回来,再向你们家里借几千块,都是这样过下来的。
当时我已经十几岁了,对父母没了工作这件事多少有一点负担,也会忧虑未来的生计问题,但想到这事儿总归不是我能左右的,很快也就不在乎了。你要知道,东北是计划生育执行得最好的地方,城市里一家一个孩子,父母都极尽可能地把你保护得特别好,所以,我的生活受影响不大。至于上一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好像他们总有办法自己解决掉。
文章作者


宋诗婷
发表文章218篇 获得19个推荐 粉丝839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