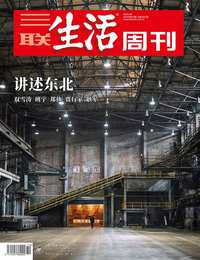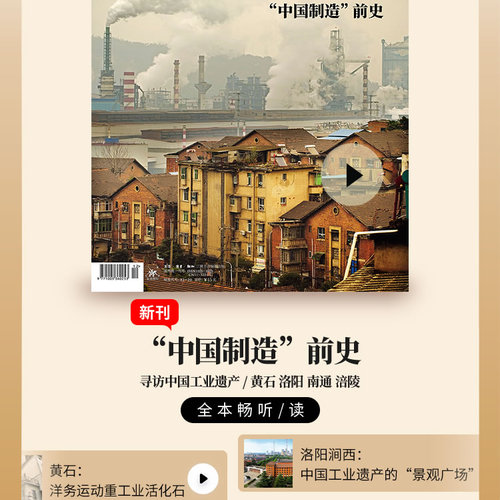阿涅斯·瓦尔达,漫长的告别
作者:张星云
2019-04-03·阅读时长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389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海滩
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新片《阿涅斯论瓦尔达》(Varda par Agnès)今年2月在柏林电影节上首映。与其说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是瓦尔达对自己毕生创作经历的一次系统回顾和阐释。她把自己曾经办过的几场讲座录像、早年间的片场花絮、剧照,以及针对每部电影的采访视频剪辑在一起,从最早的短片开始,她仔仔细细地回顾了自己的电影、摄影、装置艺术作品,讨论了创作的动力和执行方式、女性身份、数码转型等种种话题。老太太思维清晰,影片素材也组织得非常讲究,尤其剪辑点的把握堪称已入化境。
现在看来,这便是她为世人准备的告别礼物。去年柏林电影节时,瓦尔达的制片人就曾表示,瓦尔达会“放慢脚步”“准备说再见”。如今我们还没有等到这部纪录片在院线的上映,先等到了她因癌症去世的消息。
电影界也曾为她准备告别。2015年她获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7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2019年获得柏林电影节摄影机奖。去年5月,她迎来自己90岁的生日,电影界的各类人士,无论老朋友凯瑟琳·德纳芙、伊莎贝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什,还是近两年结交的新朋友、艺术家JR,都在各自的Instagram上发挥想象力,为瓦尔达送去各种充满创意的生日祝福,如今看来也像是一场盛大的网络欢送。
对瓦尔达来说,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2007年,她便拍摄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阿涅斯的海滩》,当作给自己的80岁生日礼物。
电影一开头,瓦尔达自我介绍道:“我饰演一位小老太婆,矮矮胖胖,爱说爱笑,在这里向你们诉说她的一生。”接着,瓦尔达在她的海边忙碌着,将许多面镜子摆放在海滩上,它们被海浪冲刷,反复回溯,互相映照,制造着迷人的重重幻象。她在镜头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躲进海边巨大的鲸鱼腹中,一会儿坐着轮椅行过街道。如果说《阿涅斯论瓦尔达》是90岁的瓦尔达对自己艺术成就的总结的话,那80岁时的《阿涅斯的海滩》则浓缩了她的生活:童年回忆、故地重游、老电影片段、家庭照片、她的职业、与亡夫雅克·德米(Jacques Demy)的生活,以及自己的未亡人身份。
她的一生始终与海滩有关。“如果你打开一个人,会发现风景;如果你打开我,会发现海滩。”她在电影中说道。
1940年,为躲避战乱,瓦尔达随父母从比利时布鲁塞尔来到法国南部的渔村塞特生活,在此她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期。这段地中海旁的时光为瓦尔达一生打上了蓝色的印记。后来她去了巴黎上学,在卢浮宫学院学艺术史,在巴黎美院夜校学摄影。毕业后她成了阿维尼翁戏剧节和维勒班法国人民剧院的舞台摄影师,也曾在60年代作为纪录片大师克里斯·马克的助手,随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来到中国和古巴旅行。
当她25岁决定开始拍摄电影时,她便扛着摄像机回到了童年的海滩塞特。处女作《短角情事》(La Pointe Courte)讲述的是一对巴黎夫妇在来到海边小镇后产生了矛盾。开拍前,瓦尔达没有任何拍电影的经验,阅片量不到10部,“但当时文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革命’,而在电影领域却还没有。于是我开始探索,我读威廉·福克纳的小说,读贝尔托·布莱希特,试图打破原来的电影叙事,找到一种既客观又主观的风格,让观众自由地进行参与和判断。”瓦尔达把两个相互独立的故事一章一章交替混合在一部电影里,就像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一样:一个关于渔夫的片段,紧接着一个关于一对夫妇的片段。除了地点相同,两段故事没有任何共同点。“这是私人生活和社会的对立。”瓦尔达曾说。
此片后来深深影响了法国电影。4年后,《短角情事》的剪辑师阿伦·雷乃拍出了《广岛之恋》,同年上映的还有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再过一年,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上映。正是《短角情事》这部被“新浪潮教父”安德烈·巴赞称为“自由与纯净”的电影正式开启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瓦尔达自己也曾在1962年《世界报》的专访中说:“新浪潮无论如何都会出现,而《短角情事》则代表着这一集体的第一次发声。”自此便形成了戈达尔、特吕弗等有着影迷情结的“电影手册派”与艺术家们转型的“左岸派”之间的分野,而正是在“左岸派”群体里,瓦尔达认识了另一位导演雅克·德米——她后来的丈夫。
文章作者


张星云
发表文章193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1030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