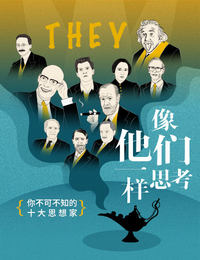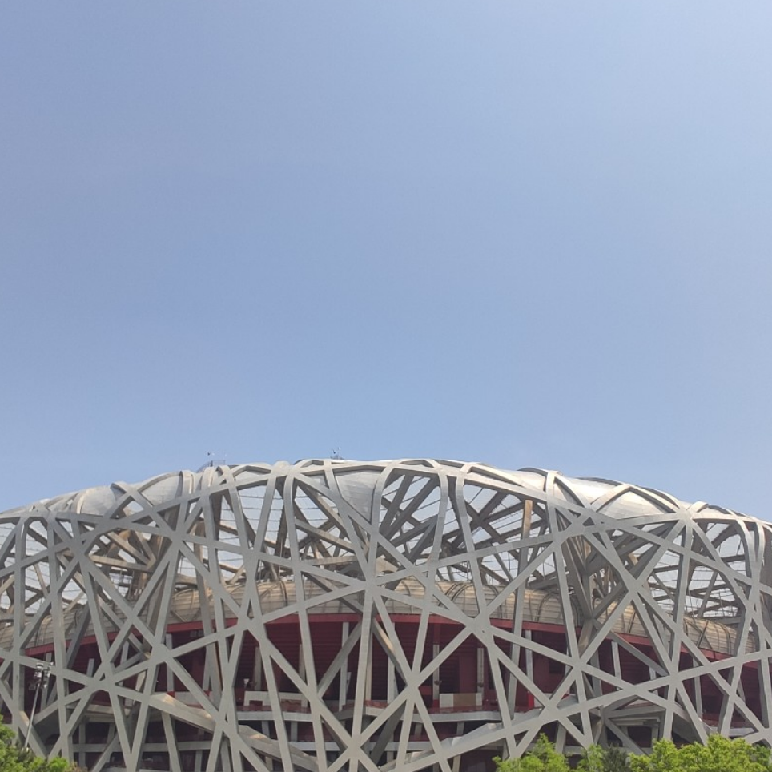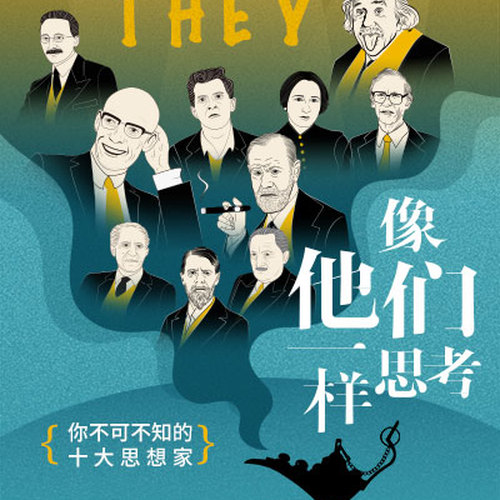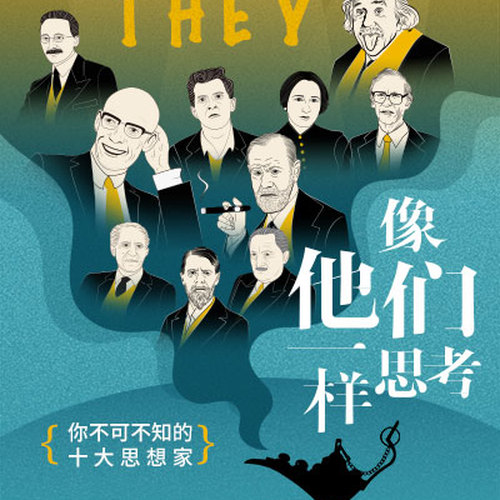1.4 总序 | 20世纪西方思想经历了什么大变局?
作者:孙周兴
2019-09-02·阅读时长3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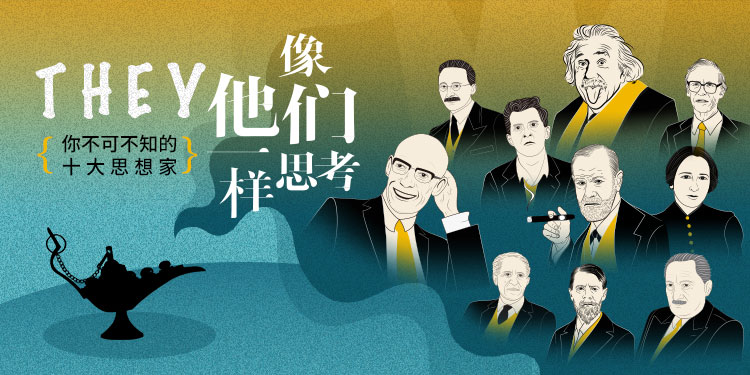
上一节我们讲了20世纪欧洲哲学的繁荣。这一节我将为大家讲讲20世纪西方思想的核心主题。
20世纪西方思想的核心主题。与传统哲学相比较,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有什么核心主题?
20世纪西方哲学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文明大变局,它的思想主题自然也变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总结出四大“现代思想主题”,即:1、后形而上学思想;2、语言学转向;3、理性的定位;4、以及理论优先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哈贝马斯认为,这四大主题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决裂。我的概括有所不同,我概括的20世纪西方思想的四个主题是:1、虚无主义,2、语言论转向,3、后现代转向,4、政治哲学转向。
第一个主题是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以尼采的说法,“虚无主义”首先意味着以哲学(希腊存在论)和神学(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崩溃,这就是尼采所谓“柏拉图主义”的消解;而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表现为基督教道德体系的沦丧,长期以来支撑和组织西方社会生活的基督教失去了效力和影响力。在尼采时代,这种情况还只是初露端倪,而我们今人则完全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了。哲学政治和宗教伦理的文化时代归于终结。我们要注意,尼采属于洞察这一真相、并且敢于公布这一真相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形态的切换角度来说,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断言不仅适合于欧洲-西方,而且也适合于非欧民族文化,比如中国。不论变局的动因如何,19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儒家传统的衰落、甚至中断,其意义完全可以等同于尼采式的“上帝死了”预判。
第二个主题是语言论转向。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说法:古代欧洲哲学的主题是“存在”,是Being,形成了古典的存在论即Ontology。近代欧洲哲学的主题是“认识”,是episteme,其理由是,如果认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问题没有解决,如何谈论“存在”?这个理由听起来十分正当。而到了20世纪哲学,欧洲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问题,理由也很简单,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前提条件,语言规定了我们的认识,我们是在语言中、通过语言、在语言的支配下进行认识活动的,决没有一种赤裸裸的纯粹认识活动。人们甚至说20世纪哲学完成了“语言论转向”。无论是欧洲大陆人文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无论是现象学-解释学路线,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诸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完成了所谓“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它们的核心主题都是语言,其他主题多半是从语言主题衍生出来的,或者多半与语言主题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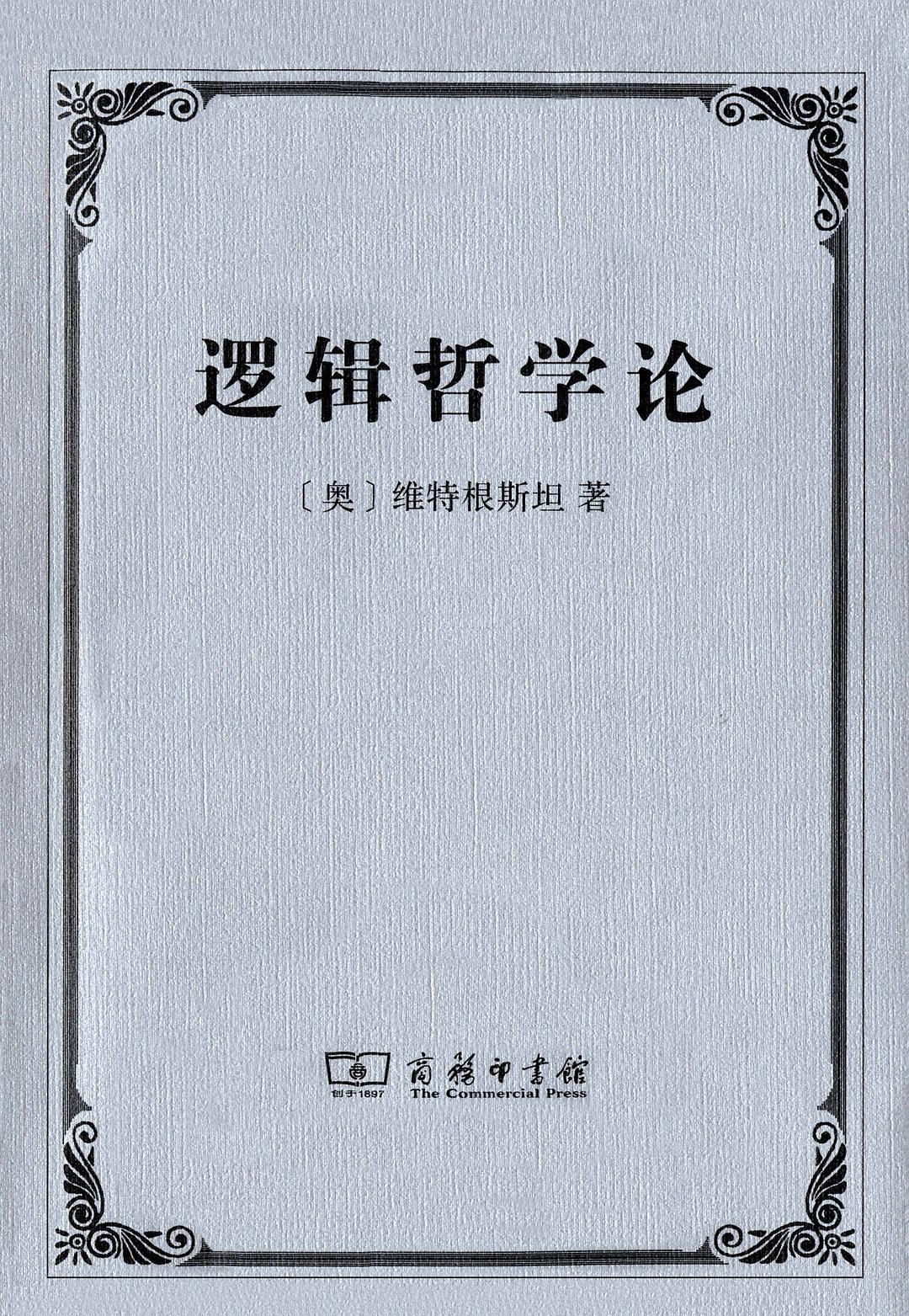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第三个主题是后现代转向。与上述“语言论转向”不无联系的,是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哲学中受到更热烈讨论的所谓“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这场讨论对于20世纪西方文化产生了殊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同样也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当代全球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本上,“后现代”是一个集中的标识,表明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技术工业已经席卷全球,成为今天世界文明的主体和主流。于是,无论是欧洲-西方文明还是非欧文明,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古今”之变:民族文化传统受到怀疑、批判和解构,传统哲学-宗教话语体系受到冲击、动摇和肢解。就现代西方哲学内部的讨论而言,上述“古今”之变首先表现为“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争论,这也是所谓“后现代转向”的核心内容。
第四个主题是政治哲学转向。“语言论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已经意味着哲学课题和哲学旨趣的重大转移。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哲学中,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浓厚的政治哲学兴趣,有人也顺水推舟,把它称为“政治哲学转向”或“哲学的政治学转向”,也有人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当今“第一哲学”。的确,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弗莱堡的逻辑哲学还保持着纯粹的理论哲学兴趣,而之后出现的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也还坚守着一种纯粹思想的性格和倾向,那么,在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哲学界、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哲学领域里,纯思的兴趣日趋减弱了,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讨论的热门。语言论转向本身含着政治哲学的动机,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的政治兴趣使语言主题的突现成为必然。正因此,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政治哲学构想中,语言哲学具有奠基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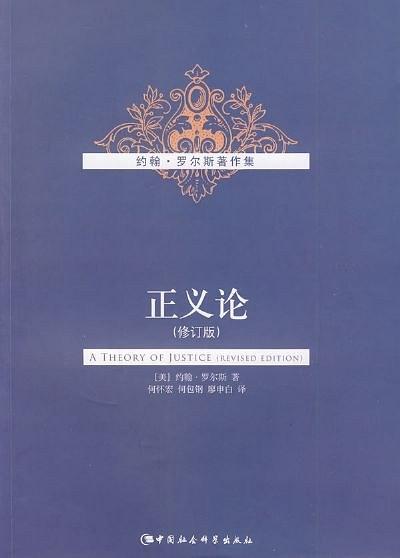
▲罗尔斯《正义论》
好,本节内容就到这里,本节音频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到文稿中查看,下一节我将跟大家讨论现代性的后果。
如果您喜欢本讲内容
可以随手保存下方海报
分享到您的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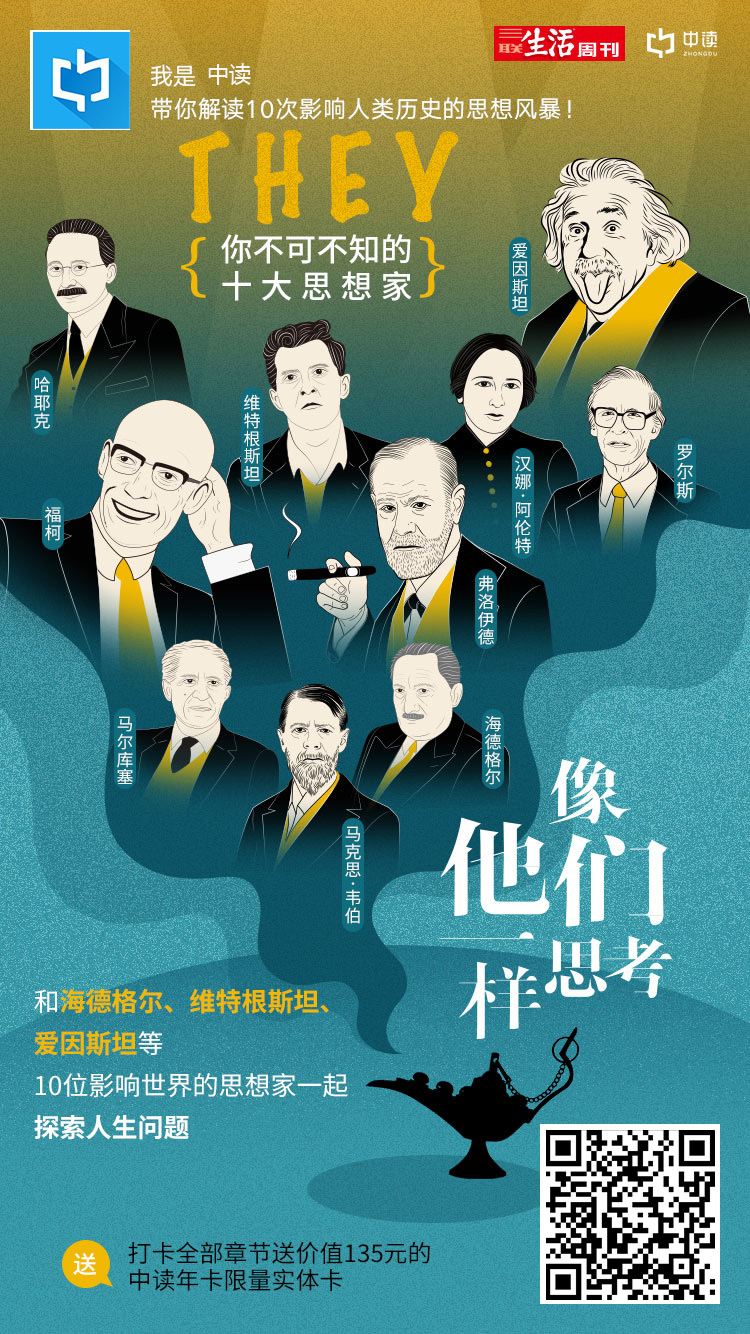
文章作者


孙周兴
发表文章6篇 获得68个推荐 粉丝861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