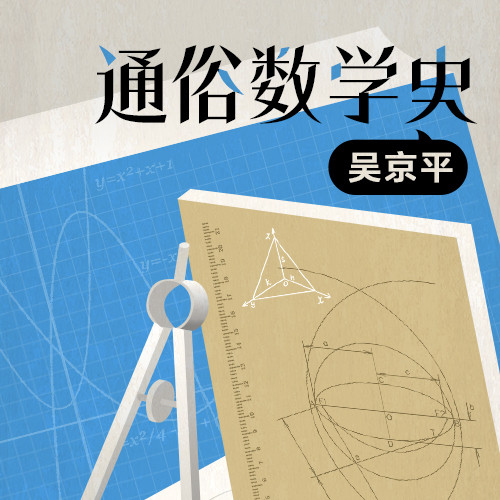关于素朴:面对路易斯·康
作者:唐克扬
2020-11-18·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901个字,产生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孟加拉国达卡国民议会厅
重看《我的建筑师》
尽管著名建筑师的个性都很强,很少有几位建筑师,能够像路易斯·康(Louis Kahn)那样,激起我写作其个人生活的念头。
开着一个商业上不算成功的事务所,康这辈子设计的建筑并不算多。我去过其中一些,另外的更多是通过书本而了解,都已有“经典”的地位。其实,尽管在设计师中有通俗的声名,一般人看不大懂他的建筑,它们的材料通常是素朴的,砖,清水混凝土,外表不“凹造型”,不算多么打眼——康的这种素朴,可算是真正的素朴,而不是像今日网红建筑一样,把素朴转化为一种视觉风格。比如,在我和他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很长时间里,我都分辨不出来他设计的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到底是哪一座楼。
但是这些素朴的建筑也不一定就是建筑工程师的菜。在他那里,一个貌似实事求是的建筑结构,就算没有任何装饰,也不见得就是符合技术理性的。比如,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康设计的金贝尔美术馆,宛如一簇有着桶拱顶盖的粮库建筑。按照建筑师自己的声言,是向发明并广泛应用了拱的罗马人致敬。但是,似乎为了满足美术馆内部空间时有连续的要求,康构想的半圆桶状的屋盖两边没法落在实墙上,也就是说,本该作为承重结构的部分却虚空了,不符合桶状屋盖一般的受力规律。工程师们换了一个思路,勉力帮助他完成了这座建筑。和外表得到的印象不同,建筑的绝大部分墙体并不受力,屋盖的四角上下承重的混凝土柱子,却看不大见;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貌似连续的摆线(Cycloid)形成的屋顶,其实是分裂的两段。因为康希望在坚实的体积内引入天光——显然,他追求的并非建筑的表象,但他也并非追求建筑的实质,这些彼此抵触的命题,顶多是“建筑的实质的表象”。
2004年,在康不幸意外去世整整30年后,这位建筑师的个人形象已经近乎被人忘却。这时,却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他与设计助理所生的私生子纳撒尼尔(Nathaniel Kahn),他执导了一部关于自己寻父经历的纪录片,叫作《我的建筑师》,获得奥斯卡提名,其中中国人熟悉的盖里(Frank O.Gehry)、约翰逊(Philip Johnson)和贝聿铭都有出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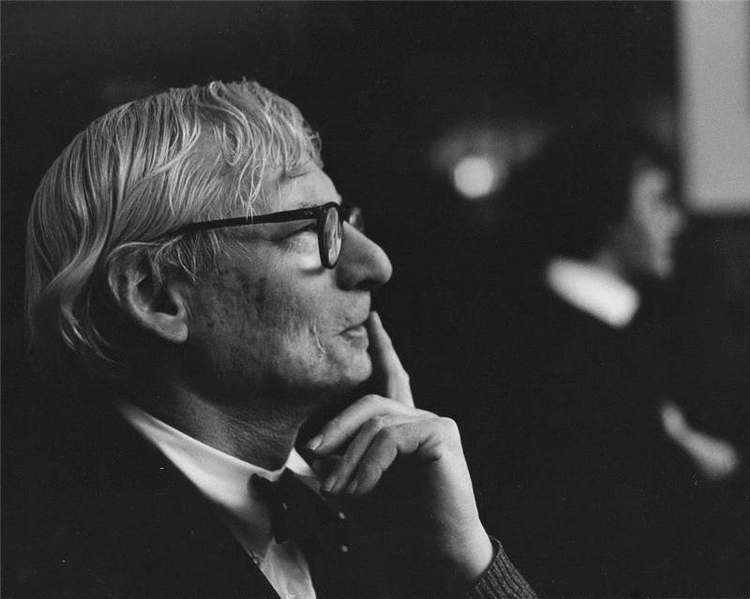
建筑师路易斯·康
在各种建筑史著作中,康的照片常常是一个轮廓光下沉思状的侧面,读者聚焦的是镜片后面深邃的眼神,他的面部特征被忽视了。我惊讶地发现,活动影像所呈现的康只是一个近乎毁容(早年留下的伤痕)的小个子。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在费城的建筑师大步穿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意气风发,自顾自地,差点把一个路人撞了一跟头,用粗鲁形容都不过分——难怪老油条约翰逊,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最著名的建筑策展人,提起他时眼里满满都是揶揄的笑意。他唐突的真人和画册里经过镜头美化的形象,就像每天都生活的房子和今天网红建筑的差别。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觉得能“欣赏”,或者,至少说是理解他的近乎笨拙的这一面了,甚至,他的伟大之处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弱点:一个糟透了的父亲和一个伟大但不完美的创造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
我们不难理解,自小缺乏父爱的私生子纳撒尼尔,为什么拍摄这部用“我的”这样措辞开头的片子。但是对于本文而言,电影放大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建筑这个行当里“非人”的这一面。康对于路人的漠然,对于自己独特理念执拗的坚持,分明是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师典型的自我分裂。早年寒微,其貌不扬,尽管一生中为世界奉献了精彩的空间,康似乎并不怎么在乎身边活生生的他人,同样,也没有过多考虑与业务无关的“别人”怎么看待他的建筑——他口中喃喃念叨的两个关键词:“静谧”与“光明”,可能与具体的人无关,尽管沉默的空间代表了无上的真理,可能和社会进步、社区营造、大众福祉等听起来无懈可击的“人类之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行业的最高目标也不妨拐向一个岔道:就像罗马建筑师曾经服务过众神和君王,康口中神秘的“光明”显然有着宗教般的自我循环的内涵。
文章作者


唐克扬
发表文章35篇 获得7个推荐 粉丝449人
设计学博士,独立策展人,唐克扬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