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行走作为阅读世界的方法
作者:肖楚舟
2022-08-30·阅读时长9分钟

接到为“行读图书奖”担任终审评委的邀请时,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正在故乡泉州带领两批学生做田野调查。两位博士生,一位在泉州近郊的永宁古镇研究城隍庙,另一位在三面临海的小岞渔村研究当地百姓祭祀祖先的传统;一批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本科生则跟着他在泉州城内做暑期社会实践。
在给清华实践项目的学生发送的课程通知中,王铭铭提出要做一场“行读”活动。十五六个学生里,只有一个是福建人,其余多对东南地方文化感到陌生。他们的任务首先是通读上世纪初,厦门大学几位前辈学者走访泉州后撰述的文献——张星烺《泉州访古记》、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陈万里《闽南游记》等,最后在这样一种阅读基础上,结合实地探访记录自己的思考。王铭铭说,想“看看他们能不能从历史中获得一些启发。在当地的生活里面感受到另一种可能”。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泉州为重点的中国东南地区便是王铭铭多次重返的田野调研地,直到2022年的今天,这里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生态仍能持续提供令他眼前一亮的新话题。在王铭铭眼中,“新知”不一定前所未见,更侧重在认知层面上去接近古老智慧的内核。他关注的人类学话题多与中国文化中的人人、人物、人神三对关系相关,致力于去古老文明里找寻现代人已经丢失的“万物有灵”的感知能力。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感受到人类对自然界的深刻影响,很多人类学家不再将研究目光局限于人类本身,而开始思考人与周边存在之间的关系。其中一系列纷繁复杂的论证被概括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近年来延伸至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乃至对“后人类的人类学”的想象。
这些人类学家的讨论与王铭铭提出的“广义人文关系”似有遥相呼应,让他不由得感到兴奋,因为“人类学终于从上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的东西里面逃脱出来,想要回到‘真问题’里面去”。所谓“真问题”,便是“怎样通过研究非现代的文明来反观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缺憾”。
面对一位倚重田野工作方法的人类学家,不免要和他谈到“行走”与“阅读”的关系,王铭铭给出一个打破成见的回答:“我们在行路的过程当中见到的事物和景象实际上跟文本没有太大的区别。旅行中的大地、天空、城镇、村庄,甚至动植物、矿石都会让我感到好奇,我会想把它们当成文本来阅读。”他说,带着这样的视角去行走,往往能获得超越个人局限和族群区隔的洞见。
王铭铭回想起他在本世纪初前往阿坝四土司地区调查途中的所见。极其狭窄的河流嵌于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公路随着河流走向曲折向前,一路风吹云动,阴雨连绵。“一下雨我就停车下来看,那一刻我看到云朵、山峰和河水的关系在瞬间就发生了改变,每一秒都不同。”王铭铭感慨,阿坝山谷的嘉绒藏民浸泡在瞬息万变的地理环境之中,自然会对人生和世界有些不同的想法,“如果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风景里面,世界观估计和现在很不一样。”
近两年来,我们的行走范围不可抗地发生了收缩。王铭铭选择泉州作为本次清华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地点,也有出于稳妥的考虑。在行走调查中解读各式各样的社群文化是人类学家的本能,那么普通人在有限的生活可能性中,又如何最大限度地去扩大身心游历的边界?
对于行走的局限,王铭铭也有过思考。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的开篇语“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让他心有戚戚,产生一种真诚的怀疑:在走向“他者”时,我们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会不会与我们的良苦用心相差太远?
书本的存在,恰好可以在避免贸然闯入的前提下补足行走不能及的遗憾。在王铭铭从中国东南到西南乃至西北的调查线索上,还穿插着其他通过书本“心游”过的神奇角落——美洲的易洛魁、祖尼、波洛洛部落,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所,东南亚的巴厘、斯里兰卡、吴哥,东西方之间的“黄土地”,环北极圈,游牧人的亚洲。王铭铭讲过一个故事。某一次欣赏完高原的险峰后,他随意走进一家书店,发现一本口述史,讲述者是一位1914年出生的彝族老人。这本小册子装帧粗陋,但里面蕴含的古朴智慧,仿佛一座智识领域的“香格里拉”,比奇峻的美景更令他振奋。
在这重意义上,“心游”未必不及“身游”深刻。王铭铭将书本理解为想象的翅膀,认为人应当通过阅读形成某种“换位”。他常在课堂上教学生阅读各类经典,但总会强调读书不是为了重复书中的内容,而是要从中获得研究的想象力。失去化所见为所思的想象力,便无法为现象赋予意义。“阅读和想象本应该相辅相成,它会让我们的智识生活更丰满、更完善、更快乐。”
三联生活周刊:从人类学者的角度出发,你如何定义“新知”?
王铭铭:现在我们听到“新知”这个词,除了理论层面以外,一般还会想到关于新技术、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现象或事物的知识。
首先这个“知”代表的应该是“知识”,跟“智慧”不同。智慧的种类并不多,可以说相当有限,但其具有长久甚至永恒的真理性,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意义。而“知识”有一种不断更新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提出的“新知”如果指的是“新的知识”,我希望能赋予它更深刻的接近“智慧”的意义。它在层次上不应该等同于智慧,但可以说是一些对从前早已存在的智慧的唤醒或焕发。
其次“新知”应当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它既有专业性,也有可读性,还对其他学科有所启发。比如我们这次评选上的文学类获奖书籍《技术大全》让各位评委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位文学家的视野跨度非常大,他用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自然、人文、社会三大领域关系的历史转变,预见了不少当下才出现的变化。
另外“新知”不应当拘泥于新旧之分。我认为“崇新弃旧”是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们应当在“新知”和“古老的智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拿这次“新知”类别的两本获奖书籍来说,《从灵光殿到武梁祠》讨论了一个特殊的艺术史阶段,里面的很多知识,比如当时的祭祀制度、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王莽在文化制度上的创造,这些我们现代人都已经遗忘。而《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则是人类学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本书,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遥远之处有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那里的人们主动选择避世主义,只靠仪式神话和世界观就能过他们的日子,生活在我们认为是“幻想”的状态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你曾与大卫·帕金(David Parkin)院士有一场讨论谈到现代性的问题,比如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极端化倾向等现象。现代人想要获得“新知”究竟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了?
王铭铭:我记得一位前辈说过,20世纪以来人类表面上取得了许多科技进步,但只是技术上的延伸,实际上在理论思想层次上绝没有超过20世纪初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获得所谓真正的“新知”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必为了日常生活中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做法沾沾自喜,以为那就是“新知”。
如今我们似乎越来越容易获得“新的信息”。一方面有了更多获得知识的渠道,一方面也更容易误以为这些未必准确的知识就是“新知”。我们变成了许多个独立的个体,不再依靠交流获取知识。现在信息的过度流通实际上也可能在阻碍“新知”的出现,这的确是一个让我感到有点担心的现象。
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模仿现代性中的一个局部。这次获奖的书籍里有一本《现代性及其不满》,它告诉我们西方的现代性其实一直有两个分支,即现代性与对其“不满”两种姿态,现代性是正反两面构成的。但我们不知为何近一两百年来一直在发展现代性,忘了“不满”。因此我主张不要过于“崇新弃旧”,一味求新,而要从中找到一种平衡。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理解“行走调查”与“阅读”的关系?你对“行读”结合的探索过程看似是自然发生的,其中有哪些有意识的探索?
王铭铭:应该说我对“行”和“读”这两个词的辩证还是一向很感兴趣的。刚好这次图书奖的名字也叫“行读”,应该说是我对此很有共鸣。“行”和“读”给人一动一静的感觉,似乎是对立的,但我认为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行和读不应该割裂来看,而是相辅相成的。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著作都来自于行走。比如研究原始文化的人类学家泰勒的著作《原始文化》,表面上看是根据别人提供的二手材料写成,但是跟他早期在墨西哥的旅行也有深刻关系。
我在旅行中想的是,大地、天空、城镇、村庄,甚至动植物、矿石都会让我感到好奇,我会把它们当成文本来阅读。我们在行路的过程中见到的事物和景象实际上跟文本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能老是文字中心主义,好像没有落成文字就不值得我们去琢磨了。
我的“行读”经历可以说是有意识的,也可以说是偶然的。最初因为我从英国毕业回国,英国人类学习惯于把中国的汉族文化当作中国一切的来源。回国以后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费孝通先生是我们所的灵魂人物,他就说我这个不行,我的中国观是错的。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他建议我去做一些少数民族的研究。这是必然的一面。1999年我们的社会文化高级研讨班在昆明召开,认识了很多当地的人类学家,我就带着学生做了一些调查,这是偶然的。做完以后我就转移到了四川、贵州、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地。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1998年到2000年间还去意大利和法国东南部的乡村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当时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王铭铭:那些调查按说是很有企图心的。为什么想去?是因为我觉得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概念词汇来对他们进行一种文化翻译。
人类学研究者做的是民族志,而民族志就是去一个地方调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把你所看到、听到、体会到的东西传递出来。留学生或留学过的人习惯于把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情况、体会到的东西,用外文写给外国人看。另一些同行即使不是写给外国人看,只是写给自己的国民看,用中文写在核心期刊发表,也习惯地用外国人发明的那套哲学或是社会思想语言。
20多年前我去欧洲试着做民族志调查,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候,用中国的语言去翻译欧洲的乡村文化。比如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社会”,和我们中国人说的“社会”是不同的,我们的“社”和“会”各有自己的含义。我们能不能用中国的“社会”去理解他们的“社会”?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有的一个好奇心。
人类学家要做的就是把别人的文化翻译成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当中的人能够理解的文本。所以我当时去欧洲做的那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调研,而是有点像一种“行为艺术”,是一种表达,它旨在表明,我们到了应该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入围“行读图书奖”终审名单的书里,哪几本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王铭铭:我很感激初审和复审的专家选出了这些好书。除了那几本获奖的书之外,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有以下几本。
一个是《我们这一代人:金斯堡文学讲稿》。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翻开这本书我才发现金斯堡作为“垮掉一代”的精神领袖,居然在美国一个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大学当老师,很奇特也很震撼。
另一本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它里面一个情节的大概含义是,野性的文明化过程(至少在这本最古老的史诗里面)跟女性的作用是有关系的,这跟我们在西方人类学里读到的东西不大一样,也非常有意思。
另外还有《但丁传》。但丁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甚至圣人,但传记里面恢复了但丁作为佛罗伦萨人的面貌。包括他跟当地权贵的交往,跟自己家庭的关系,他的个人命运,把他从神坛上降低为一个平常人。它甚至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写的地方史,但是把但丁放在地方史里面,这是我们一般学者不大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兴奋。这些书都是对我的“无知”的一种补充。
(参考文献:王铭铭,《心与物游》《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魁阁的过客》《他乡故土间:我的身游、心游与“乡愁”》)
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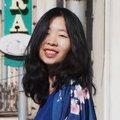

肖楚舟
发表文章0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