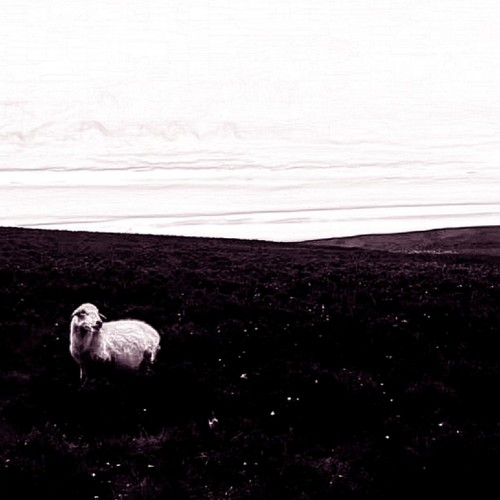“走!喋碗泡馍去!”
作者:明根
2018-10-26·阅读时长5分钟
T.Y.明根吉雅(裕固族)
西安的夏天不适合吃羊肉泡馍,太燥热!而到了初冬,一个阴天的中午,正好饭点,饥肠辘辘,一出门,四面八方的冷风都往脖颈里灌,厚棉服还没来得及穿,单薄的衣裳挡不住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这种时侯,捧一碗热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呼呼下肚,便能让你从脸庞到双手,从喉咙到脏腑都舒坦坦的暖和起来,紧缩的脖子也伸展开来了。
羊肉泡馍这种食物有极强的地域风格,你看,西安肉夹馍、凉皮、臊子面等等之类,在省外其他地方不管是否正宗也都有得卖,唯独羊肉泡馍,作为一种最具代表性的西安美食存在,在我眼中,相当于北京的豆汁,爱恨分属两边,所以,在外省是极少见有卖的。当然,人们对羊肉泡馍的接受程度虽然远大于豆汁,但如果不经历若干年秦地饮食文化的熏陶,外地人是不太容易喜欢上这个食物的,从前,我就吃不惯。

我的家乡在祁连山深处的群山草原,那里的人们从来不把牛羊肉炖到入口即化的样子再吃,老人们说:煮烂的肉吃了不消化,牛羊肉一定要有些嚼劲吃起来才最好。这个道理我觉得,大概是由于游牧民族多年来吃肉的习惯造成的。在家乡吃羊肉,通常都是大铁锅盛着大块肉,满满一锅咕嘟嘟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满锅肉将将熟透就可以大盘子捞起,手把朵颐而快之,而已经炖到软烂的肉,经牧人的口腔感知后通过大脑传输反馈,判断为已至可吞咽程度,随咽之,从而剥夺了食物在咀嚼的时候口腔分泌消化酶的过程吧!草原上的游牧人觉得,劲道的羊肉配上清亮的羊汤是上等的美味,而泡馍,讲究的就是肉烂汤浓。祁连山与秦岭,相距虽只有两千公里的地域差距,对于羊肉如何才算好吃这件事上,判断标准却大相径庭。

汪曾祺的《人间滋味》里有一句,我觉得确是有理“有些东西,本来不吃,吃吃也就习惯了。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
第一次吃泡馍,是2002年,那时,我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被请去西安知名老字号“老孙家”去品尝本地特色,什么味道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面对眼前那然然呼呼的一大碗,怎么都尝不出"美味"二字,本想表现的礼貌一点,至少吃完眼前那一碗都做不到。之后很多年再没碰过这种看起来既无颜值,内涵又不明显的食物。
第二次吃那是08年在西安上班以后。有天和同事去找他的一位朋友办事,到了中午饭点,对方要请我们吃饭,几番推辞后决定就在门口简单吃碗泡馍。同事的朋友五十多岁,有大把的社会经验以及人生冷暖要表达,说到激动处我只看到,桌子对面,阳光的光束里,从他口中喷出残渣无数,于是,那顿饭更是让我对羊肉泡馍敬而远之。
我开始接受它就是在那样一个初冬的中午下班,大家都下楼要去吃饭。
“今儿这天冷飕飕地,想喋碗泡馍,走!一起?” 一个同事说。于是,本想拒绝这个食物的我,架不住冷风天里对一份温暖的渴望,竟缩着脖子蹴着肩膀跟着去了。单位周边方圆三公里以内至少有四家泡馍馆,同事带我去了一家略远一点的,名曰“伊俊斋”,说他们在这家吃了很多年,味道好。
泡馍馆里,门口发号牌的大姐通常都会对常来的老主顾莞尔一笑,麻利的递碗、放馍、发号,除非你特意交代要现成的馍,否则,大家都默认为自己掰。掰出馍丁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服务小哥和后厨师傅对待你这一碗的态度,见到一碗掰的均匀细碎的馍,后厨师傅便会有一种对上了接头暗号一般心领神会的默契感,确认为这一碗馍的客人是“自己人”。我曾经怀疑过端回来的碗不一定就是我所掰的那一碗,但其实,后来发现,这种担心完全就是多余,可能性微乎其微。
前桌的两位阿姨,一边细细的掐着馍丁,一边慢慢聊着自家那些糟心窝子的事,一肚子苦水倒完了,馍也掰好了,等几分钟,煮好的泡馍上桌,刚倒完苦水的肚子刚好被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馍填满,心满意足后,互相告别归去。我觉得,这样的小聚对于两个阿姨的含义,其实跟两个小白领相约在星巴克轻声慢啜一杯咖啡并无二异。面前的那一碗汤色奶白,缓缓升着热气,我把一双冰凉的手捂在碗边上,如同捧了一个暖水瓶。自己掰的馍丁被后厨加工后似乎能储存双份的温度,又然又烫,我一开始为了所谓优雅的吃相坚持用筷子夹起碎馍丁小口食,吃了几口我就发现这不行,根据我从小吃羊肉长大的经验,这样吃,等着我的就只有温吞吞索然无味的羊肉汤了。于是放弃讲究,学着同事那样,用筷子轻轻拢起最表面的一层馍吸入口中,果然,既吃到热乎的煮馍还不至于烫到舌头。从这次以后,泡馍在我的脑海里便种下了一个温暖的记忆。
说到吃东西时要不要发出声响这件事,我以为,一要看吃的食物,二要看在哪里吃。《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写过一篇《食物的分贝》,说到“今天的人们已不再用色、香、味老三样来衡量美食,他们喜欢用“风味”这个词,强调的是感官以及心理的复合感受,这其中,当然包括声音感知”。你是否还记得?在看《舌尖》的时候,导演也确实将食物入口和吞咽的声音做了夸张的处理,而这样的效果,让观众从视听两方面感受到了食物的美味。因此,有些食物,还真不必过于讲究吃相,如果不能全心享受食物带来的乐趣,岂不也是一大憾事。
要说,到底哪家味道更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西安人对某家泡馍馆的喜爱,与兰州人对某家拉面馆的喜欢是类似的。在兰州,每个人都有他们钟意的拉面馆,有的人天不亮就起个大早,就为了"马子禄"的那碗头锅面,有的人穿越半个城就为了喝一碗"安泊尔"的牛肉汤,更多的人,也许小区前面路口的第三家牛肉面馆,就是每天上班前雷打不动的早餐。而在西安,那些如“同盛祥”“老孙家”之类的老字号大店,从来也都是招待客人的地方。自家附近的,某家说得上或者说不上原因就合自己口味的,才是经常光顾的去处。偶尔,周末时间充裕了,可能会去城墙根下,小时候常去的老巷口那一家,只为了那熟悉的味道入口时,味觉记忆瞬间带回的童年时光。
有时候,我一边掰着馍,一边看着馆子里忙活着的回民大姐和跑堂小哥,总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也许是与我那千里之外的某个兄弟姐妹相似的褐黄色的眼睛、自来卷的发梢,或者是同样羞涩的笑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在这个包容的城市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在食物、长相和语言中的借鉴、融合和交流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
又是一年冬来到,西安的初冬总是细雨绵绵,供暖的日子似乎又总是遥遥无期,天阴沉沉湿漉漉的到处都弥漫着寒意。
“饿不饿?”
“吃撒?”
“走!喋碗泡馍去!”
文章作者

明根
发表文章7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4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