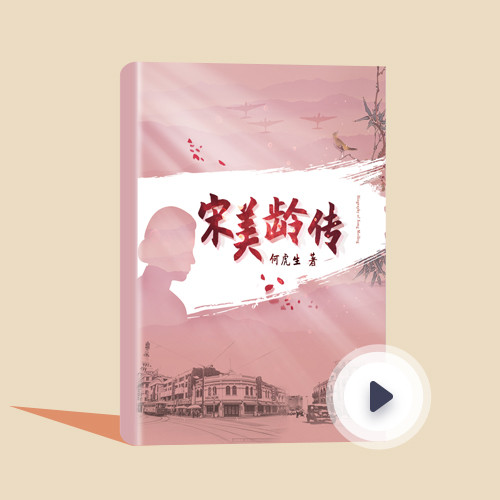新西兰寻鲜记:阳光、时令与乡愁
作者:吴丽玮
2019-01-23·阅读时长3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8517个字,产生3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摄影/黄宇
海:富足的精神家园
当北半球正是冰雪隆冬时,在盛夏中的新西兰街头,圣诞装饰的橱窗里,圣诞老人正戴着墨镜跟驯鹿一起坐在海滩边晒太阳。
我跟朋友约好去海滩捡蛤蜊,地点在奥克兰北部旺阿帕劳阿半岛上的莎士比亚地区公园。眼前的风景本是新西兰的日常,但让我哪怕看一百遍,脑子里仍会不断浮现出本地人爱说的那句,“景色美得真令人窒息”。脚下是青葱的草场与树林,十几只绵羊聚集在一棵新西兰圣诞树下躲太阳,这种毛利语叫做Pouhutukawa的高大乔木在每年12月至次年1月开花,满树红火,非常喜庆,于是被当地人叫做圣诞树。翠绿蜿蜒起伏延伸到远处蔚蓝的海面,天空则是另一种澄澈,白云仿佛海尽头的山丘,与奥克兰海面上的朗伊托托火山岛并行排列。红、白、绿、蓝,每一种色彩都饱和醇厚,大地、海洋与天空,则组成了这个纯净海岛之国的标志符号,一种回归自然的淳朴之美。
能捡到蛤蜊的地点是公园里的一处弧形沙滩。挽裤腿撸袖子,扎紧帽子挎上小桶,走在泥滩上,觉得“赶海”二字特别贴切。沙滩沿线的海底遍布滩涂且非常平缓,潮涨潮落,落差有几百米,那些营养丰富的淤泥之中,正有无数鸟蛤静静地生长着。趁着退潮,把手伸进泥里,每掏一把都有丰富的内容。
这是一处免费捕捞的公共海滩,当某一种物产泛滥之后,类似的还有螃蟹、生蚝等等,免费捕捞政策听上去相当诱人。但每一处都会有限额,鸟蛤的限额是每人50个。把捡到的鸟蛤倒在滩涂上的小水流里淘洗,贝壳上原本的色泽和线条逐渐呈现出来,像水墨画般清雅。挑出最大最饱满的50个,剩下的归还给海洋,这是本地人的自觉,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毛利人来说,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之情更为明确。“我们会在捕捞之前,感激掌管大海的神,感谢她为我们提供食物。当我们装满了,提不动了,要立即停下,绝不多拿,否则将会受到神的谴责。”在基督城采访Fush餐厅老板、毛利人安东·马修斯(Anton Matthews)时,他这样告诉我。
新西兰大大小小的海滩几乎都有公共电烤架,蛤蜊抬上来,直接铺在烤架上烤。几分钟之后,它们缓缓地张开,里面的肉质嫩得剔透,别烤太干,也不用加任何调料,鲜爽足矣,还有那长久浸润的海水的味道,吃进去感觉特别饱满。
对生长在海边的新西兰本地人来说,这样的海洋总是会让人产生满足感。当我们对新西兰的印象停留在《指环王》与《霍比特人》里的中土世界时,本地人会温和地纠正你:“草原很美,牛羊肉很美味,但大海和海鲜才永远是新西兰人心中的第一。”
虽然是主要英联邦国家之一,华人在新西兰的比例也非常高,但作为一个南太平洋上的遥远之岛,中国对它的了解还仅限于新世界的美丽想象之中。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移民国家之一,与亚洲和欧洲相比,这里有关人的历史非常短暂。大约1000多年前,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从波利尼西亚的故乡哈瓦基(Hawaiki)来到新西兰。1642年,荷兰人亚伯·塔斯曼奉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命来到这里,他为新西兰贡献了一个新名字Nieuw Zeeland,意思是“新的西兰省”。西兰省是荷兰两个知名航海大省之一,遵照荷兰的另一个航海大省荷兰省的名字,大洋洲另一片新大陆被命名为Nieuw Holland,不过这个名字最终被“澳大利亚”所替代,但新西兰保留了它原有的名字,尽管新西兰跟荷兰的西兰省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直至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库克带领船队抵达新西兰,这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欧洲人对新西兰的移民和殖民历史。
虽然欧洲人的脚步迟到了很久,但当库克船长踏上这片“长白云故乡”时,世界航海进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他初次登陆新西兰同年,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新的世界观,从新西兰被发现时就埋下了种子。

在《历史的视角:新西兰与海》一书中,作者弗朗西斯·斯蒂尔分析道:“蒸汽船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帝国扩张的性质和力量出现转折,同样也标志着人类对于海洋的理解发生了质的转变。西方传统观念认为大海是恐怖、敬畏与排斥的代名词,很少有人能跨越大洋,这些人的目的也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去寻找新的资源和新的市场。但蒸汽船的出现让人类在面对海洋时获得了极大的自信,19世纪轮船制造业开始工业化生产,轮船企业进入公司化运营时代,这二者促进了英国海洋立法的加速发展,在同一时期,捕鲸业的飞速起步也让遥远的公海成为大陆生产车间的延伸。英国人发现,在横跨太平洋的运输网络里,通过大洋洲的航道比苏伊士运河更有优势,这也让新西兰有机会从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航运网络中解脱出来。”
作为“新世界”的新西兰,无论是源自于南太平洋岛国的毛利人,还是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当他们共同组建一个新的国家时,两者的海洋观并没有什么冲突。弗朗西斯·斯蒂尔写道:“整个19世纪,因为海洋在国际交流、运输、贸易、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实力增强,人们关于海洋的诸多文学艺术想象被激发出来,于是,海洋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化迷恋’。大洋洲被定义成‘一片有岛的海洋’,而并不是‘被海洋包围的陆地’。在新西兰,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可能跟其他地方都不同,在新西兰人的生活世界里,大海是三维的:它是储存着家族血脉联系的历史空间;是交通中一个令人生畏的领域;是一个工作区,也是一个休闲区,同时也是一个十足的想象空间。”

海鲜:关于食物的记忆
新西兰人对大海的热忱,其中必然少不了对海鲜的迷恋。而说到海鲜,归根结底又无非是“新鲜”二字。“少即是多”,越是新鲜,越不需要多做什么,这个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新西兰,最有代表性的海鲜之一就是贝壳类的生蚝和蛤蜊。奥克兰知名的休闲餐厅Depot即以这二者为最大的招牌,生鲜吧摆放在餐厅显著的位置,在层层叠叠的碎冰之上,一年四季都会有来自不同海域的生蚝和蛤类新鲜供应。新西兰南北两岛有很多产蚝区,每个地区生蚝的成熟季不同,北岛的奥克兰产区及更北的凯利凯利,每年3月率先开启各种生蚝狂欢派对,而到了5月,则是南岛最南端最著名的布拉夫生蚝收获的季节,这让新西兰人一年四季都有福可享。
这天供应的两种生蚝分别来自奥克兰以北的玛胡兰基半岛和更靠北的奥郎格湾,蛤选择的是新西兰南岛最北端马尔堡地区的Tuatua。每一个慕名而来的食客,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点几只无异于海边石头的硬壳做前菜,接着再拿起菜单看看要吃些什么。厨师拿着小刀“噔”一声撬开贝壳,客人端起一角,“咕”一声吞下,全过程结束,但却是Depot最为精彩的一幕。

生蚝的外壳质地就像一层层剥落的岩石,边缘处卷起与粗粝感极不相称的波浪曲线,诉说着它每一次被海浪拍打的痕迹。玛胡兰基半岛生蚝的个头稍大,厨师撬开一半外壳,蚝肉几乎盛满了内部的空间,在阳光下泛着丝绸般的奶油色泽;奥郎格湾的生蚝外壳略薄,但从内部看却泛着金属的青光,让蚝肉顿时有种很名贵的感觉。虽然是“咕”的一口闷,但已有足够的时间让人分辨生蚝的不同。生蚝自带一种狂野之味,刚刚撬开外壳,蚝肉仍满满地沉浸在类似海水味道的汁水之中,入口的一瞬间,关于它所经历的阳光与风浪的故事,全都在那绵软的些许韧劲中讲述出来。生蚝简单撒上一些柠檬、黑胡椒末、葱末与红酒醋调和的汁,用酸来平衡海水的味道。相比之下,玛胡兰基半岛的生蚝更咸,但肉质也更浓稠,奥郎格湾的生蚝更加清冽,肉更绵软,于是对于两片海域的自然环境有了不少想象和猜测。
生蚝很棒,但我更喜欢Tuatua。Tuatua是新西兰的一种肉粉色蛤类,一般这种叠词的名称都是毛利人用自己的语言起的。生蚝的外壳在大自然的洗礼中变得凌厉沧桑,而Tuatua的外壳则在海水的冲刷下显得珠圆玉润,肉质就更加诱人了,也是亮晶晶的肉粉色,跟几只生蚝一起盛在简易金属盘的碎冰上,显得格外馋人。同样扬起脖,一饮而尽,Tuatua的肉质筋道,嚼起来,清脆的感觉从牙齿一直传到了耳朵里,非常享受。脆让牙齿很有发力感,但终究有海鲜的那种柔软度,甚至带着小小的甜味,而随着每一次的咀嚼,淡淡的海水味才逐渐释放出来,清脆中透出被海水抚慰过的温柔细嫩的感觉。
Depot的食材选择出自于餐厅老板艾尔·布朗(Al Brown)的个人喜好。之所以格外青睐玛胡兰基半岛的生蚝,是因为当年他曾造访过当地一家生蚝农场,跟农场主一起驾着小船到生蚝种植区挖生蚝,一边喝新西兰著名的长相思葡萄酒,一边大快朵颐。因为那次经历太美好了,艾尔总是会怀念那时生蚝的味道,“对于新西兰人来说,‘食物的记忆’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艾尔的家在新西兰北岛东南部,距离首都惠灵顿不远的小镇怀拉拉帕,他跟两个姐姐在农场里长大。艾尔说,新西兰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我至今记得3岁的时候,我看到我爸和他的伙伴一起跳上小船出海,因为不能带我去,我当时失望极了。后来在大概4岁的时候,终于开始学抓鱼了,我家附近有条小水沟,我常去那抓鳗鱼。”艾尔说,那时他抓鳗鱼的工具特别简陋:把一根钓丝缠绕在一颗点火石上,拿一颗螺丝当坠子,再垂一根吊钩,上面挂上一小块羊肉杂碎做诱饵。“我会在河边观察,哪里的淤泥里有一个漩涡,或者在有一排柳树的岸边,那些用树叶遮盖住的小水坑里,八成就会有鳗鱼。”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最有趣的周末活动就是全家出动去海边钓鱼和露营。“在我的印象里,我们从没有空手而归过。每一次都会有一两条嘉华鱼,有时再多一条鲂鱼,银鳕鱼和唇指鲈鱼的可能性也很大。”满载而归之后,这一天便会在悠闲中度过。退潮的时候,孩子们跳进水里撬鲍鱼的壳,抱着冲浪板一头扎进浪里,或者拿着5分钱欢天喜地地去买棒棒糖。当太阳开始缓缓落山时,用巨大的废旧汽油桶改装的烤架下点起了火。“空气中弥漫着烤鱼的味道,大家聚在一起,女士们喝着杜松子酒,男士们豪饮大罐的冰镇啤酒。我呢,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看各种露营车来来往往,有些车停了好几次,但都没法把拖斗准确地泊进位置,家里人于是吵了起来。”艾尔说,“海边活动对于新西兰人太重要了,可以说大海和鱼已经是新西兰人DNA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钓鱼和海鲜,我想新西兰人的魂儿也就丢了。”
而作为灵魂的一部分,新西兰人对海鲜也是相当地怜惜与博爱。


在新西兰北岛东海岸的霍克斯湾,其中心城市内皮尔有一家名叫Bistronomy的简洁餐厅,菜单上有一道叫做“12公里白鱼”的招牌菜,老板兼主厨詹姆斯·贝克(James Beck)解释说,“12公里”指的是内皮尔向海洋延伸12公里的范围。“虽然可能水没那么深,鱼的品种也有限,但我还是宁愿用这里的。”詹姆斯说,“如果用很远的鱼,长途运输过来会消耗很多能源,我觉得没必要。”给他的餐厅提供海鲜的是当地一对渔民夫妇,詹姆斯介绍说,他们原本是在大渔业公司工作,后来辞了职,想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捕鱼。“他们用的是一种自己设计的很大的金属渔网,网眼很大,还可以伸缩,可以让小鱼游出去。”在新西兰,总是能遇到很多有情怀的人,詹姆斯与渔民夫妇相互选择,看重的是与对方相同的理念。“大的公司会用渔网捕鱼,首先,网子里非常拥挤,会挤坏很多鱼,浪费严重;其次,鱼挤在一起会非常紧张,当它们拼命挣扎时,体内会释放出大量乳酸和皮质醇,这会让肉内有血水,味道不好。而他们使用的这种渔网,可以将浪费减少到5%。”而除了渔网的设计优势之外,减少浪费的另一个主要做法是,像Bistronomy这样的餐厅会将整批鱼照单全收,“鱼一旦离开了水,成活的概率几乎为零,我如果不买,鱼就只能浪费掉了”。
詹姆斯说,在保证新鲜的前提下,其实只要处理得当,便宜的鱼依然会非常美味。在中国人看来,活蹦乱跳才是新鲜,这和新西兰人的理解有偏差。他们和日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保证新鲜,必采取活缔之法,即当鱼被捕捞之后,要用正确的方法尽快结束它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吃小鱼的大鱼,如果肚子里有没消化完的小鱼,不处理很快就会坏掉”。詹姆斯说,渔夫在捕到鱼后,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一颗锐利的长钉打入鱼的脑部。“因为很快,鱼感觉不到痛苦,把对它的伤害减轻到最低。而且鱼也不会紧张而让肉质变差。渔夫会把剖出的鱼肠丢出去喂海鸥,接着把鱼头冲下放进冰水中放血,这样可以让鱼肉在熟成的三五天内,依然能够保持新鲜厚实,不然的话,鱼肉会变得非常松散。”
这天他收的是别人会嫌弃的“便宜货”柠檬鱼,是鲨鱼的一种,肉比较柴。詹姆斯把鱼段烤好之后,用各种酸和甜与之搭配:大黄根茎是本地白人喜欢的一种蔬菜,样子类似于芹菜秆,詹姆斯做成了甜酸味;还未成熟的青草莓,采摘下来进行发酵腌制,吃起来非常清新爽口;另外再撒一些腰果,跟肉的柴组合是一种奇妙的互补;最后整盘菜浇上熬入接骨木花的橄榄油,让柠檬鱼肉自带花香,也因为酸甜和油的滋润,烤过的柠檬鱼味道变得更加香喷喷了。
文章作者


吴丽玮
发表文章100篇 获得6个推荐 粉丝411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