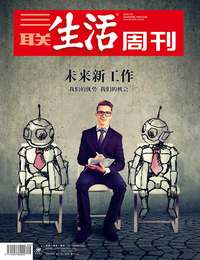珠峰大本营行记:在山的阴影下
作者:陈晓
2019-02-21·阅读时长3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8626个字,产生6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一切都在抖动
树木、田地、房子在抖动。山在抖动,天空在抖动,身下的座椅、身旁的舷窗,都在抖动,我甚至能感觉飞机的零件正在窸窸窣窣裂开。
“这该死的小飞机!”我在心里狠狠骂了句。这种短距起降的小型通勤飞机专属于偏僻航线,在山地乱流中的稳定性很差,失事率也高。但我们现在身处的卢卡拉到加德满都的高空,只能选用它,这是喜马拉雅山区里能接受的最大型交通工具。
每当剧烈的抖动让恐惧从心底涌起时,我会不自觉地看向前面那块半遮的布帘。帘子后面是驾驶舱,掩映着驾驶员的侧脸。我盯着他,想从他的身姿和神情上观察出飞机是否失控。驾驶员也在抖动,蛤蟆镜腿、侧脸和半个肩膀,都随着机身上下颠簸着。但还好,他并不慌张,甚至有点气定神闲的懒散。
其实,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离开了卢卡拉机场,安全升上天空。卢卡拉是尼泊尔萨加玛塔国家公园的大门,也是进出珠峰地区的入口。机场由第一位登上珠峰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捐资修建。如果没有它,到卢卡拉最快的方式是从加德满都出发,乘3天汽车,再徒步5到6天。机场将加德满都到这里的时间缩短为半个小时,不过代价是颠簸和危险。

卢卡拉机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据说大大小小的事故已经达到两位数以上,绝大部分都发生在飞机起降时。机场只有一条跑道,460米长,不到国际标准跑道的十分之一,和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跑道长度相似。不同的是,如果在航母上降落失败,还可以拉起复飞,但卢卡拉群山环伺,只有一次降落机会,而且地面没有导航设备,只能靠飞行员的目测和经验。即便建造者给跑道加上了18.5度的坡度设计,增加飞机起飞的加速度和降落后的阻力,但前后逼仄的群山仍然是凶险的杀手。1975年,埃德蒙·希拉里的妻子和女儿就因为降落时飞机撞上山崖殒命。

只有亲眼看到这个机场,才明白人类是如何在方寸之地,将自己快速进入喜马拉雅中心的意志和严酷自然强行嫁接。倾斜的跑道一头连着断崖,另一头是山谷,对面就是巨石屏障模样的群山。一般下午三四点以后,机场就进入“关门时间”,大风和云雾随时可能灌满山谷,阻挡航道。赶上雨天,机场周围更是愁云惨淡,数天不散。每个对珠峰心怀幻想的外来者,无论是进入还是离开,都得忍受群山喜怒无常的折磨。
我们从加德满都去卢卡拉时就被折磨了几回。早上6点多赶到机场,去卢卡拉的柜台前已是人头攒动,挤满了前几天延误航班的滞留客人。候机室里更是热闹,露胳膊露腿的欧美登山客们在候机厅里玩扔瓶子的游戏消磨时间。当他们的声浪几乎掀翻狭小候机厅的房顶时,当地人就在旁边安静地坐着。披挂传统纱丽的女人,拿公文包的黝黑皮肤男人,涂抹大红唇膏但眼神低垂的年轻女孩,都略有些木讷地沉默着,好像他们才是这里的客人。
预订机票的起飞时间毫无意义,我们在机场等了两天。加德满都4月末的阳光洒下来,照得整个停机坪明晃晃、白亮亮。我们隔着候机室的玻璃等,坐在跑道边的摆渡车里等,在狭小逼仄的机舱里等,呼吸着黏稠闷热的空气,从清晨到下午,等待着属于我们的那个可以起飞的幸运时刻。
要离开它也同样不容易。徒步结束后,我们又在卢卡拉待了两天。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评估今天雾气和阳光的比率,满足飞行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机场的围栏边,总坐着一群期待回到文明世界的徒步者,像鲁滨逊遥望大海另一头的大陆那样,眼巴巴地望着短短跑道后的浩瀚群山。
后排传来呕吐的声音。密集且强烈的抖动中,时时夹杂着猛地一沉,飞机好像在乱流中勉力维持着某种不可能达到的平衡。我闭上双眼,努力将抖动的群山、谷地、河流关闭在意识之外,将身子沉下来,融进飞机的抖动中。“不要抗拒它,跟它在一起。”我在心里劝慰自己。
在如机枪子弹一样密集的战栗间,群山从舷窗外哆哆嗦嗦掠过。洛子峰,卓奥友峰,马卡鲁峰……还有如金字塔顶般敦厚壮实的珠峰,像一朵朵跃出海面的白色浪花,自云层中隐约浮现。每年有3万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忍受这段颠簸危险的航程,就是为了看到它们。

山的诱惑
这片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曾经是海底,属于特提斯海域。大约1800万年前,这片海域将印度板块从亚洲大陆分离。沙砾、珊瑚残渣和无数的海洋生物尸体层层沉积,堆砌在海底。
海底如何变成高山?简单地说,就是无限时间和巨大力量的结合。印度板块的北部边缘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向西藏板块的南部边缘移动。当两个边缘合拢时,大量积聚在海底的沉积物被挤压在一起,热量和压力使它们石化,几十亿吨新鲜岩石被板块撞击的力量强行推出海面,经年累月向上驱动,形成四个弧线山脊,这就是喜马拉雅。
走在喜马拉雅山间,就是走在特提斯海的海底,触目皆是千万年前那次板块撞击后的遗留物。随着云雾浓淡聚散,山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态出现——有时候像一张巨人的脸,悬在头顶上方的浓雾中,威严地微微颔首;有时候像一大面顶天立地、勃勃生长的生命体,看不到尽头;有时候云雾太重,只能看到脚下的黑色碎石,如海水漫无边际,好像走在某个阴暗荒凉的外星球。突然阳光破空而来,驱散浓雾,才发现咫尺间尽是高山,披冰挂雪,威风凛凛。
所有这些山之中,珠穆朗玛无疑最具传奇性。它的外形并不出众,体型过于矮胖宽大,线条也略显粗糙,远不及一些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秀美。但世界第一高度和至今仍在向上生长的生命力,让它成为最能激发人类想象力的一座山峰。
这块由闪着银光的冰雪和暗色条纹状岩石构成的巨型石锥,是不同时代勇敢者的游戏。自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从南坡登顶以来,人类共开辟了19条不同的登顶线路,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向山峰冲击。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曾被认为“飞鸟都无法飞过”的北坡登顶。1963年,美国登山队横穿珠峰——从南面登顶,由西南山脊转北壁下撤。1980年,“登山皇帝”梅斯纳尔单人无氧登顶。2004年,“战斗民族”俄罗斯人“死磕”北壁,从中央直上登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珠峰的游戏已经延展到山脉之外。1990年,澳大利亚人斯内普(Tim Macartney-Snape)开始了一项名为“从海到山”的探险——他从海拔0米的孟加拉湾海边出发,历时3个月,徒步1200公里至珠峰脚下,再从南线单人无氧登顶。
这是世界第一高度激发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是人类精神对从黑暗海底崛起到喜马拉雅阳光下的自然力量的回应。早期对珠峰发起挑战的是英国人。从1921到1924年,在灵魂人物马洛里的带领下,英国人三次试图登顶珠峰。彼时正是工业革命之后,机器震撼并改变着人类社会,山是唯一可以与机器抗衡的自然物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弗朗西斯·荣赫鹏曾将马洛里和同伴们三次冲击珠峰的记述整理成《珠峰史诗》。他在书中这样描写珠峰的诱惑以及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登珠峰意指爬上去——用自己的腿爬上去,整个要点就在这儿。只有这样,人才能为自己的本事感到骄傲,而具有好本事又多么令灵魂感到满足。如果我们老是倚赖机器,而不锻炼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我们就这样失去生命中的许多喜悦——那种能淬炼我们的灵肉以臻完满境地的喜悦。
所以,回到起点吧!决定攀登珠峰是一种常见的冲动,就像想去爬邻近一座山丘那样。攀爬珠峰所需要的努力巨大得多,但仍是同样的那股冲动。的确,与珠峰相搏是精神想要战胜物质的一场缠斗。人,这个神圣的存在,就是想让自己优于物质,甚至最强大的物质。
文章作者


陈晓
发表文章26篇 获得12个推荐 粉丝789人
社会调查、徒步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