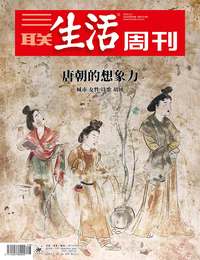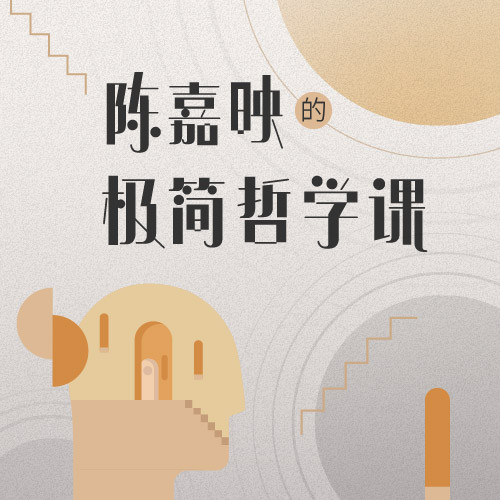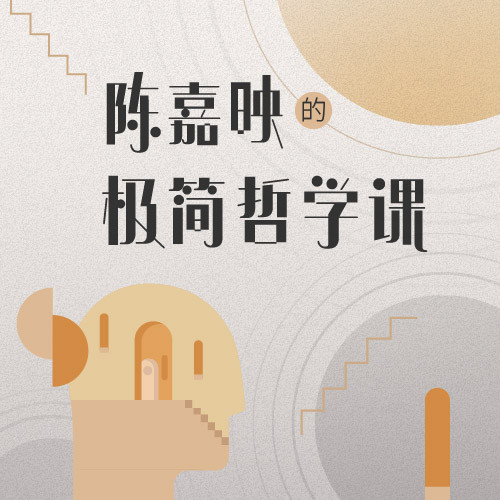“一战”百年,分裂的纪念群像
作者:刘怡
2018-11-28·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100个字,产生1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情形高度类似,这是一场属于法国的独角戏。2018年11月11日中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等8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陪同下,马克龙冒雨穿过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主持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悼念活动。在那块建成于1920年的墓碑前方,常年摇曳着长明火,以示对法国及其殖民地在大战中阵亡的140万将士的怀念。在悼念仪式上,马克龙发表了语气尖锐的演讲,直称“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并且警告“旧的恶魔正在死灰复燃,准备继续完成它们制造混乱和死亡的工作”。有鉴于此,法国愿意继续和各国一起,承担“增加希望,而不只是反对恐惧”的重任。
有两位重量级人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缺席了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集体徒步游行。在1919年为缔造战后世界秩序而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一个不曾出席,一个沦为配角,与“西欧中心”的基调显得格格不入。一个世纪之后,特朗普和普京虽然出现在了凯旋门下,但似乎更加看重彼此间的双边关系,互相握手寒暄不已。对他们来说,在巴黎配合马克龙的演讲不过是礼节性举动,月底在阿根廷G20峰会上的会面才是重中之重。正在忙于说服内阁接受“脱欧”方案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缺席了在巴黎的集体活动,仅仅出现在伦敦的纪念集会上:100多年前,是英国政府对比利时独立地位的维护和对法国的倾力支持奠定了协约国获胜的基础;而在一个世纪之后,伦敦与西欧的关系却正在变得微妙和疏远。
同样抗拒加入“西欧中心”叙事的还有东南欧各国。在他们各自的历史话语中,1918年11月11日首先是作为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标志性节点出现的,是19世纪以来持续抵抗帝国主义支配的结果,与西欧诸国对“自相残杀”往事的痛惜属于两个概念。在波兰,莫拉维茨基总理出现在了庆祝第二共和国诞生100周年、充斥着反俄口号的群众集会上。英超俱乐部曼联的塞尔维亚中场马蒂奇拒绝佩戴带有哀悼意味的红色虞美人徽章,原因是“西欧国家从来不曾支持南斯拉夫在大战之后的统一,最后还在90年代摧毁了它”。而在中东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与以色列国防军爆发了新一轮军事冲突。他们的矛盾源头可以追溯至“一战”末期的《贝尔福宣言》;对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来说,那场战争至今仍未结束。
整整100年过后,全球各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解依然可以归入两个大相径庭的阵营。西欧诸国基于新的一体化共识,已经可以坦然接受大战作为集体悲剧和集体教训的结论,并将追思历史作为开启新合作的基础。但对大部分东南欧国家来说,大战给予他们的独立和自决在20世纪曾屡次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干涉:首先是巴黎和会上的挫败,接着是“二战”前后的边界安排修正与雅尔塔体系,最后则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局部冲突。他们更愿意将本国确立主体性的历程描述为民族主义的正面功绩,而不是在“人类大同”的语境下对其加以贬损。而美国态度的变化,影响尤其重大:一个世纪之前,是伍德罗·威尔逊以一己之力向西欧兜售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但在英法帝国主义和本国的“领域分离论”支持者的夹击下遭遇挫败。而在2018年的今天,另一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成为拒斥多边主义与集体行动的先锋。纪念活动中出现的分歧折射出的已经不单是各国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差别,它同样反映了在大战结束100年之后,美欧对现实世界的迥异看法。
马克龙的弦外之音
短短11个月过后,马克龙在就职之初营造的“美法共识”愿景似乎已经悄然退场。他那篇声色俱厉的凯旋门前演讲,看似在回顾历史,话锋却直指特朗普关于“美国第一”的种种表态。在来自84个国家的代表注视下,马克龙尖锐地指责道:“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一旦抛出‘我们的利益第一,谁关心别人’这类言论,就抹杀了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也是赋予它以生命力以及不可或缺的存在——它的道德价值观。”听到这番话的人们当然会想起,就在一个星期以前,特朗普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集会上曾经公开宣称:“你们知道什么是全球主义者,对吧?全球主义者就是那些希望全球变得更好的人。但坦白讲,他们不那么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你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吗?我们不想要这么一伙人。”
而特朗普“不想要”的,正是马克龙在纪念仪式上竭力主张的。法国总统诚恳地承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当时的法国政府对历史教训的认知依然是肤浅的。即使那场战争造成了将近3000万的军人和平民伤亡,即使战争对欧洲经济和人口的摧残使得后者逐渐远离了世界政治的中心,法国人依然纵容自己的报复心和帝国情结压倒了一切。在巴黎和会上,克列孟梭总理及其支持者先是推翻了美国方面基于民族自决、贸易自由和公开外交的新秩序安排,竭力要求在中东和非洲继续保有足够大的势力范围;接着又对凯恩斯基于经济规模提出的复兴德国的主张(记载在他那本著名的《大战的经济后果》中)嗤之以鼻,竭力要求对德国提出惩罚性的赔款要求和经济压榨。结局自然是两败俱伤:德国经济在停战后10年已然陷于破产,对法国人的报复心理最终带来了纳粹党的上台和1939年的另一场战争。而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同样无法从“一战”以后的重建中汲取足够多的资源来支持它在东南欧和非洲的帝国理想。最终,整个欧洲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文章作者


刘怡
发表文章196篇 获得14个推荐 粉丝2496人
身与名俱灭、江河万古流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