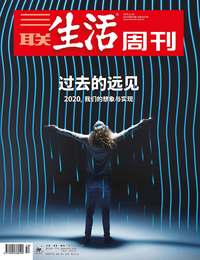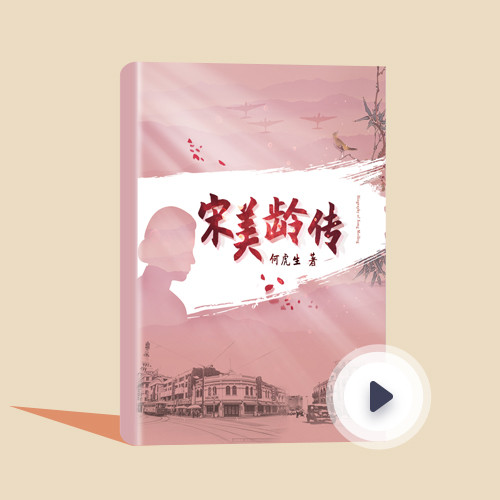当人工智能干预自杀
作者:严岩
2019-12-13·阅读时长15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759个字,产生1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黄智生,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也是自杀干预组织“树洞救援”的发起人,其志愿者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并做现实中的自杀干预(蔡小川 摄)
一条自动推送的自杀信息
“凌晨他打电话和我说,感谢你半年来的陪伴,但我等不到变好了,喝完这点酒我就跳楼了。”李虹是一个自杀干预组织“树洞救援”的志愿者,她缓慢而平静地向我回忆起最近一次成功阻止的自杀行动。
“当时他还说要跟妈妈打电话,让她听到自己儿子落到水泥地板上的声音。我立刻打电话给他妈妈,她倒是特别平静,说‘随他去,我等警察通知’。”李虹还把自杀男孩小姨的微信给我看,字里行间也劝李虹放弃他,不要再费心帮助他。
男孩叫马盛,是一个南京的大二学生,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又欠下了数笔网贷。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试图自杀数次——吃药、割腕、跳河、烧炭。每一次的自杀行为,李虹都干预了。马盛第一次吃药昏迷后,李虹等人立刻报警,南京警方找到他后送入医院,这才算挽回了性命。
回溯李虹和马盛命运交织的时间点,来自一个自动监控并发送“自杀风险等级”的程序。制作这个程序的人叫黄智生,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去年,他在微博上发现了一个叫“走饭”的女孩,她于2012年因抑郁症自杀离世。她的最后一条微博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自此,“走饭”的这条微博的评论区成为很多抑郁症患者网络上的情绪宣泄地。过去,人们心里藏着秘密又希望能够一吐为快,会跑到树林里找个树洞,对着树洞说出秘密,然后用泥巴将装满秘密的树洞填上。如今,“树洞”在微博上出现了,其中最大的这个“树洞”已有累计超过160万条信息——黄智生想到,也许可以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来分析社交媒体的用户行为,从而更精准地发现高风险的自杀人群,并进行自杀干预。
2018年7月27日开始,黄智生的“树洞机器人”上线,每天监控“走饭”评论区的内容,并发布每日“树洞监控”,通报到各个救援微信群。根据该团队编写的《网络自杀救援指南》,自杀风险被分为10级。黄智生告诉我,“一般6级以上才会进行人工干预”。所谓6级,即“自杀已经计划中,自杀日期未明”;7级则是“自杀方式已确定,自杀日期未明”。机器先判断风险等级,黄智生再将自杀信息进行整合,并每隔6个小时推送到各个救援群一次。当时马盛发的微博便是其中一条,李虹看到了机器推送的信息,由此开始了她长达8个月的远程陪伴:微信上的沟通、经济上的支持等。她甚至说,“实际上,我除了陪伴他,还在陪伴他的妈妈和小姨”。
在这个自动监测并发出自杀预警的程序诞生以前,人们总是在新闻上获知一些自杀死亡者的信息,比如前不久自杀离世的韩国艺人崔雪莉和具荷拉。有自杀倾向的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最后一条留言常常十分隐秘,在当事人死亡之后再去看,才能看出“遗言”的样子——“拜拜”就是具荷拉留在Instagram上的最后一条信息。换句话说,要提前预知并准确解读社交媒体上的自杀信息,是极其困难的。
“我坚持不了了,我先走了!”这原本可能是马盛的最后一条信息。当天晚上,他发完微博后就服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树洞机器人”监测到了这条信息,并被发送到了救援的微信群。黄智生提道:“这个程序用的是‘知识图谱’的技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句子中的一些概念进行推导。比如‘树洞’有条评论写道:我今天决定了,明年中秋就是我的忌日。按照知识图谱的推理,会先从句子中抽取出‘我’‘决定’‘中秋’‘忌日’等关键结构,然后通过属性变换,将‘明年中秋’与‘2020年8月15日’建立等位关系,将‘忌日’对应为‘Death’来表示死亡事件的本体等,通过这些推理,将句子中的关系词映射到网络的本体中,然后通过结点之间的路径来确定目标。”简单来说,要确定一个高危自杀者,程序需要确定:是否有自杀事件;是否有具体事件;是否有抑郁情绪表达。但这个技术本身的准确率就存在上限,需要人工维护。“目前5级以上的自杀风险信息一天100多条,准确率在83%左右。”黄智生告诉我。
其实,早在2017年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有类似的课题。该课题负责人朱廷劭自2013年开始做网络心理的研究,通过用户的网络行为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变化,包括可能的自杀行为和自杀风险。“人们有时候会说,自杀是个人的决定,有人真想自杀,其实不应该拦着对方。据我们的研究,确实有21%的人不想要任何的帮助,但79%的人可能是对能否获得帮助没有信心。”朱廷劭说,“微博用户里面,青少年是主力,同时自杀又是这些青少年的死亡主因,所以我们就考虑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做自杀干预的工作。”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朱廷劭团队开发了“在线自杀主动预防”系统,不赞成做现实中的自杀干预(蔡小川 摄)
朱廷劭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观察,其实自杀者有很多不同于常人认知的地方。比如,很多人认为,在网络上说自己要自杀,通常是为了博取他人的关注,而不会真正采取行动。但通过朱廷劭团队的研究,事实上在网上表达自杀意念的人,有一半以上真的尝试了自杀。此外,人们认为自杀往往是冲动型的,其实不然。朱廷劭他们之前找到了30名确认自杀死亡的微博用户的公开数据,经分析,自杀死亡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表达有清晰的逻辑结构。“比如,‘我昨天坐高铁到深圳,今天在深圳做报告’,这就是有序列性的表达,使用频繁则说明这些人的逻辑思维很清楚。换句话说,这些自杀死亡者在自杀之前并不是思维混乱的。”
不久,朱廷劭团队开发了一套“在线自杀主动预防”系统。他们先从“网络爬虫”自动下载“走饭”微博评论区的内容,这些作为原始数据,没有任何标注。后续再利用机器学习的模型,对每一条微博给出一个预测标注,自动去标注这条微博是否有“自杀意念”。“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不同等级的区分:有自杀意念、有计划、有实施。自杀意念的表述有‘我这种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计划的表述是‘哪天受不了了我就跳下去’,有实施就是‘18号我就选择离开’。”朱廷劭补充,“但汉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增加了机器识别的难度。比如,‘饭饭,我很快就要看到你了’,如果这条信息发布在‘走饭’的评论区,那就会被认为是有自杀意念的;反之,如果是在其他场景下,则没有自杀意念。现在这个模型仍需要不断地优化,目前预测模型的精度在80%以上。”
中科院的这套系统与“树洞救援”的核心不同点在于,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未经过高危自杀者的同意,朱廷劭团队的志愿者不会进行现实中的自杀干预,不会有类似李虹等志愿者长达8个月的陪伴。朱廷劭告诉我,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们考虑到心理救援的边界,即“助人自助”,如果有自杀意图者不想接受帮助,志愿者不会擅自行动。“通常来说,我们会给对方发送私信,内容除了自我介绍,还会提供三种干预信息:一是提供网站地址做心理测量;二是提供全国心理危机干预的热线电话;最后也告诉对方,如有需要,我们有志愿者在线值班等。”
朱廷劭反复提及,“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救了多少人。自杀问题太复杂了,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
文章作者


严岩
发表文章0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86人
记者/编辑,播客爱好者。偶尔尝试一些不会死人的极限运动,刺激杏仁核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