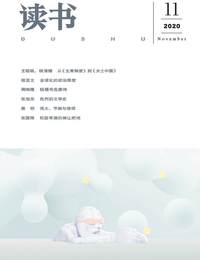超越“无用”与“变异”
作者:读书
2020-11-27·阅读时长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393个字,产生6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王 勇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说法叫 “法学幼稚 ”。此后很长时期内,这个说法被填充不同的内容而用于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评价,包括他评和自评。这其中,法理学是一个经常性的批评对象,典型的批评意见集中于法理学缺乏对本土问题的回应能力,缺乏 “中国问题意识 ”: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范式都与本土法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法理学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被长期质疑,在如火如荼的法治建设实践大潮中,法理学持续遭遇 “什么是你的贡献 ”(苏力),“向何处去 ”(邓正来)的诘问,乃至于几乎陷于宣判 “死亡 ”(徐爱国)的境地。而在重整 “法理 ”(张文显)寻求 “再生 ”(季卫东)的过程中,塑造中国法理学 “合法性 ”基础的努力始终与法理学的实践立场关联在一起。
法理学源于关于法律的一般性理论认知,以及关于法学的一般性概括,前者是基于直接对象的判断,后者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对诸如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等部门法学的提取公因式般的概括。在这两个层级上,法理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及理论存在形态都面临前述 “实践观 ”稀薄的批评。就法理学的实践观而言,在第一层级方面,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两种类型不同却有着高度关联的 “映射思维 ”上。第一个是 “法律 ”或“法治 ”对法学及法理学的 “映射 ”:法律发展的实践状况要求学理对其做出积极性回馈,做出抽象性评价,这种回馈之中包含了后文提及的“合法性添附 ”在内的多种理论和类理论诉求。第二个是人们的道德与情感等对法律及法学的 “映射 ”:以超负荷的 “法治理想主义 ”或“法律万能主义 ”心态向法治和法理学提出需求。
关于第一种 “映射 ”,也就是法理学的知识生成第一个层级,表现为法理学与法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就此方面,有一种近乎直觉和本能的集体性认知: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中国法治建设共享着同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背景。法理学既是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一种合法性论证和智力性支持,同时也是具体的法治实践及更为宏大的国家治理实践在法律理论上的映射。在此过程中,法治实践为法理学的知识生产界定了语境与任务,由此构成了法理学知识生产的动力源。
从一般意义上说,实践催化并定义理论,这其中的充分性无须太多论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彼此交织的过程中,法理学的知识生产,实际上来源于两种颇为不同甚至具有紧张性关系的驱动或需求:其一为法治实践对法理学所提出的基于法律和法治自身内在逻辑的理论需求。其二是非基于法律逻辑而向法学所提出的理论和 “类理论 ”需求,其经常性地表现为就某种即时行为向法理学提出的 “合法性添附 ”的要求,要求对此做出符合某种特定预期的解释,通过 “理论 ”修正或 “覆盖 ”“僵化 ”的字面规则,从而迎合外于法律而在的集体情绪。
法律来源于生活实践,而法律也超越生活实践,法律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决定了并非全部的生活实践都能够向法律和法理提出作为的要求,反之亦然,而法理学亦然。但这个 “超越 ”的对象和范围不甚清晰,“法治理想主义 ”和“法律万能主义 ”的情绪驱动着法理学的更新速率和面貌。就此而言,从知识来源方面看,法理学具有非自足性的一面,它需要法治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支持,从而获得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结构,外理论而在的实践,驱动着法理学的知识生成 ,也规定着法理学的知识类型(法价值论与功能论)与知识属性(合法性论述)。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55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