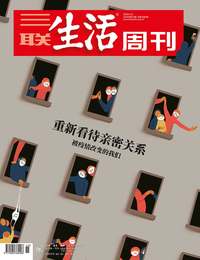和面团相处,和自己相处
作者:黑麦
2020-04-08·阅读时长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081个字,产生3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在厨房里研究面团的象象
2月15日左右,北京的疫情似乎开始有所缓解,不过街上依旧空荡荡的,外卖平台上可选的餐食仍不多,有时候还需要早起抢购。突然间,微信里蹦出一条信息:“哥儿们,想吃酸面包吗?”问我的这个朋友名叫象象,在去年的一次饭局上,我听他讲起自己最近开始做面包的事,想到自己当天的晚餐还没有着落,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了“想”。
当天晚上,我们选择了在人流最少的时间交接,我戴着口罩骑着电动车,在街上搜寻着另一个戴口罩的同龄男子。不一会儿,一个拎着纸袋子的人出现在马路牙子边,我伸手接过他递来的面包,紧接着加了把油,骑回家。
洗干净手,我打开了面包的包装,一个带有树叶形割纹的棕色面包冒了出来,沉甸甸的,散发着麦子烘烤过的香气。在几乎没有面包房营业的日子里,能吃到刚出炉的酸面包,是一种小确幸,于是,我一边吃一边和象象聊起了他烤面包的故事。
其实酸面包并非什么稀罕物,它不过是由一块名为“酵头”的酸面团所制成,在面包的世界中,“酵头”就是中国老一辈人做面食时喜欢用的老面肥,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面粉和酵母的工艺得到发展,速成制品越来越多,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再使用这种酸酵母了。那些养了数十年的面团,也在岁月中变得稀少。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西海岸成为世界美食运动发源地的时候,“有机”“从农场到餐桌”“无麦麸”等等观念从这里兴起,酸面包和它年轻的信众们也从这里开始发迹。那些喜欢发酵的人,有的投身自酿啤酒,而另一些人则开启了酸面包烘焙坊的营生,这些人有个统一的称呼——“潮流客”(Hispter)。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也由此衍生出了“发酵节”,以及“替出差的人看管酵母的工作”等新鲜事物。当我和象象聊起这些的时候,他似乎从来没有关注这些,至于为什么下厨房做面包,他所给出的答案也非常简单,“就是想在隔离期间,和自己独处一次”。
象象说这是他第一次“玩儿进去”。在这段时间里,象象通过做酸面包,在社交网络上结识了不少朋友,他用新鲜的面包和各种美食爱好者们置换辣椒酱、青团、植物的种子和自酿的葡萄酒。他所说的这些经历,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起这位认识了许久的朋友,因为这些年来,象象的变化不大,他似乎一直都是老样子,短短的头发,戴个眼镜,不胖不瘦,话不算多,见人就笑,无论冬夏,都喜欢穿黑色的T恤,始终保持着他最初在苹果店时的样子。好像也是从做面包开始,象象重新认识了自己。
在疫情发生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让自己陷入种种消息营造的情绪氛围中,一方面他关注着经济的动向,另一方面,他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在厨房里。按他的话来说,每天除了做饭、洗碗,还要花上三四个小时和面团打交道,随着面团表面的起伏,睡觉、醒来,有时候,他的太太也会参与进来,与他一道完成面包的出炉。“对于我来说,这是疫情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象象说。
文章作者


黑麦
发表文章231篇 获得14个推荐 粉丝2335人
沉迷于对抗中年危机的美食作家,对groove着迷的音乐编辑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